突尼西亚非常迷人。这个国家的北海岸,吹着宜人的岸边海风、下着绵柔冬雨;内陆的平原和南方的沙漠,则闪耀着温暖的艳阳,自古以来吸引了无数访客到此一游。从创立了迦太基的古老腓尼基殖民者,到摩尔人旅行家利奥·阿非利加努斯(Leo Africanus),再到欧洲的旅行家、艺术家、冒险家,诸如大仲马(Alexandre Dumas)、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伊莎贝尔.艾伯哈德(Isabelle Eberhardt)、王尔德(Oscar Wilde)、赫胥黎(Aldous Huxley)、克利(Paul Klee)、纪德(André Gide)、沙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突尼西亚都对他们盛情款待、展现迷人风情。
这也难怪萨夫万.马斯里,会对突尼西亚情有独钟。
对萨夫万来说──我在这里把他叫得这么亲密,不光只是因为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同事好多年,所以真的很熟之外;这种轻松亲近的感觉,正是这本书的精随所在──突尼西亚对萨夫万来说,不只是一段可爱的小插曲,也不只是想要画进某幅画里面的壮丽风景,或是某个故事情节的有趣设定,更不是像我以前也曾经一度认为的,只是一个适合进行某些社会科学研究的场域。以上这些,都不是萨夫万心中的突尼西亚。对萨夫万来说,突尼西亚是他心中纠结已久的未解之谜,而这本书正是他下定决心,想解开这个谜团所顺带产生的成果。
如同萨夫万自己也承认,《突尼西亚:阿拉伯世界的异类》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正式的社会科学学术作品。这本书本质上,就是他自己想从突尼西亚这块,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看到的愿景和谜团里,用一个主观、切身的观点去了解他自己、了解这个社会,才写出来的作品。而且也因为有着类似想法的人不只他一个,所以这本书也对于在辩论当代阿拉伯世界的传统与现代,或是文化正统性和文明纷争的这类讨论,有所贡献。
萨夫万在约旦出生、长大。他的双亲是穆斯林,他的母语是阿拉伯语。他至今都还是跟他住在约旦的亲朋好友感情很好。为了增进当地青年的教育机会,他也已经跟约旦的哈希姆王国政府密切合作了好多年。不过真正让他人生改观的,还是他在美国求学、授课,还有担任大学职员的美式生活。在美国文化的熏陶之下,他有机会而且也被期待,在专业上展现企图并追求成功。他当然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可是他同时也发现了自己可以而且被期许,去追求他做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我实现。后面的这种期许恐怕就是美式生活中,最出其不意却影响众人至深的一大特色。他深深受到古典的美式自由主义影响,强调个人自由、社会平等、道德普遍主义和隐含在其中的乐观主义。他已经成为了肯尼迪总统在一九六○年所描述的「自由派」:
……他们放眼未来而不留恋过去;他们拥抱新知而不会故步自封;他们关心社会大众的福祉,包括公共卫生、居住正义、教育环境、就业情况、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他们相信外交政策的僵局和疑虑,是可以被突破的。
这些价值似乎已经展现在萨夫万自然流露的自信和热忱当中,但这些特质在今日的阿拉伯世界里仍旧少见。取而代之的是焦虑和怀疑,以及满满的怯懦、守旧和随之而来的惴惴不安。
大概只有突尼西亚是个例外。
突尼西亚乘着后来我们所知的阿拉伯之春而起,看起来是唯一一个顺利摆平革命后暴力和反动余波的国家。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都没有幸免于难。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阿拉伯之春会从突尼西亚揭开序幕?为什么它的影响又是在突尼西亚比较「后继有力」?而且为什么当其他国家陆续加入突尼西亚的行列想摆脱暴政,结果却陷入内战或是招致另一派的军人干政时,突尼西亚却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国家机构的改革,并为了寻求社会不同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在自己的国内展开有时比较激烈,却鲜少暴力失控的辩论和对话?
突尼西亚的经验是不是如同突尼西亚人,和全世界所希冀的如此「成功」,现在还无法下定论。就像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一九七三年季辛吉访华时,被问到三百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什么时,所留下的名言:「现在还言之过早。」的确,突尼西亚对一个公民的、竞争的政治环境,还有一个可问责政府的希望,也不是没有被高高举起,然后重重摔下过。像在二○一○年到二○一一年的革命期间倒台的突尼西亚前总统班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二十五年前刚上任的时候,就曾给过突尼西亚这种美好的期待。
不过驱使突尼西亚人民走上街头、扳倒统治者,然后对于想要一个怎样的政府和统治者,去进行社会内部辩论的这种风格和精神,真的太特别了。特别到萨夫万因此在这本书里,提出这个萦绕在他心头已久的疑问:突尼西亚到底是怎么把他青少年时期,很熟悉的阿拉伯习惯和传统,跟他后来成年时,在美国才接触到的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去芜存菁、兼容并蓄的习惯,其实是突尼西亚一直以来的特色。诚如突尼西亚的第一任总统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在他的民族主义论述里,一直强调突尼西亚的「地中海型人格」:突尼西亚本身就是一个交叉路口、一个混血儿、一个合成物。
对萨夫万和其他许多人来说,让突尼西亚这么独特的原因五花八门,恐怕要出版一整套,充满感情和想象力的论文集才有办法解读,所以萨夫万就在这本书里尽可能地尝试了各种答案。他考虑突尼西亚的地理位置。突尼西亚紧邻非洲萨哈拉沙漠的北缘,并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相距不过九十英里。他也回顾自古以来在突尼西亚这块土地上,朝代更迭、留下了各自足迹的帝国王朝:迦太基、罗马、拜占庭、柏柏尔、阿拉伯、鄂图曼以及法国。他检视伊斯兰教在突尼西亚历史上和信仰上的在地特色,以及突尼西亚在十九世纪跟东鄂图曼和欧洲接触之后的互动过程,最后则是二十世纪民族主义运动,对突尼西亚造成的影响。他检视突尼西亚独立后,在总统布尔吉巴带领下,坚定不移的亲西方路线,以及布尔吉巴确保宗教的某些反智思想,不至于阻碍经济发展、影响女权奠基和教育扩张的坚定决心。毕竟萨夫万大部分的人生,从求学到后来担任教职都是在学校里度过,所以他也很自然地看见,突尼西亚从十九世纪延续至今一连串的现代教育改革,是他们之所以成功的一项关键要素。
萨夫万不是唯一一个,说突尼西亚是「阿拉伯世界中的异类」的人。《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在评论突尼西亚二○一四年大选的时候,就曾说突尼西亚「很明显是中东地区的异类」。来年,在诺贝尔和平奖颁给「突尼西亚全国对话四方集团(Tunisia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的记者会上,委员会做出了如此评论:「在二○一一年一月,独裁的班阿里政权垮台以后,突尼西亚就走向了一个非常独特、令人惊艳的发展」,他们的获奖理由如下:
首先,他们证明伊斯兰份子和世俗政治的社运人士,是可以为了国家的最佳利益携手合作,并达成意义非凡的成果。突尼西亚的例子彰显了对话的价值,以及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认同,在这个冲突频仍的区域里有多重要。其次,突尼西亚的转型也展现了公民社会里的各个机构和组织,可以在国家民主化的过程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虽然在艰难的情况之下,他们依然能往自由选举与权力和平转移的方向迈进。「突尼西亚全国对话四方集团」的成就值得被肯定,也肯定他们当初想透过茉莉花革命,带来正面改变的初衷。
突尼西亚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们总是让人对他们充满期待。显然诺贝尔委员会并不觉得,现阶段就肯定突尼西亚已经转型成功是「言之过早」。虽然当年独立之后的突尼西亚,曾经让人燃起跟这次类似的希望;在班阿里上任初期,也曾让人有过这样的期待。不过当然我们只能说,希望那些对突尼西亚现在发展充满信心的支持者不要再次失望。我承认我对突尼西亚早先的发展曾经很失望,所以现在心中是有点担心和怀疑的。记得那个时候班阿里刚上任不久,他曾推动一个政治协商的「国家协议」,以彰显他当初说要建立民主政府的承诺。当时我还写下我对这个国家协议的满心欢喜,特别是因为当时刚刚民主转型成功的拉美国家,都是以国家协议的方式做为转型的第一步。所以我就乐观地做出一个结论:
突尼西亚的国家协议,是突尼西亚人民强调并庆祝他们凝聚力的一种努力。展现他们对伊斯兰传统的崇敬,和对国家民族的骄傲,同时亦承认并鼓励不同想法和利益的多元并存。这个协议不但没有将保守的偏差价值,带入后来建立的政治关系中,我们甚至应该将这个协议理解为他们正在努力培养,对异议和反对意见的容忍这块民主政治的基石。这个协议本身,只是朝向实质民主前进的第一步,一个体制的转型还有许多路要走。这个协议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可以带着突尼西亚人民走到哪里,而是他们会因此往哪里前进。
这个乐观的看法才短短几年的时间,就被证明是大错特错。突尼西亚政府后来,变成了世界上最专制的盗匪国家之一。原本让这么多人都满心期待的突尼西亚政府,原来只是公关手腕太高明、太会包装,让我们都信以为真。全世界的我们这些热爱突尼西亚的人,包括旅行社、代办业者和简直太好骗的国际金融机构等等,就这样完全没有注意到突尼西亚落入贪腐和暴政的深渊,最后导致二○一○和二○一一年间的示威抗议。
现在我们只能希望那些还在唱衰突尼西亚的人是错的,而萨夫万对现在突尼西亚转型的乐观评估是对。希望突尼西亚的改变,不会再走回头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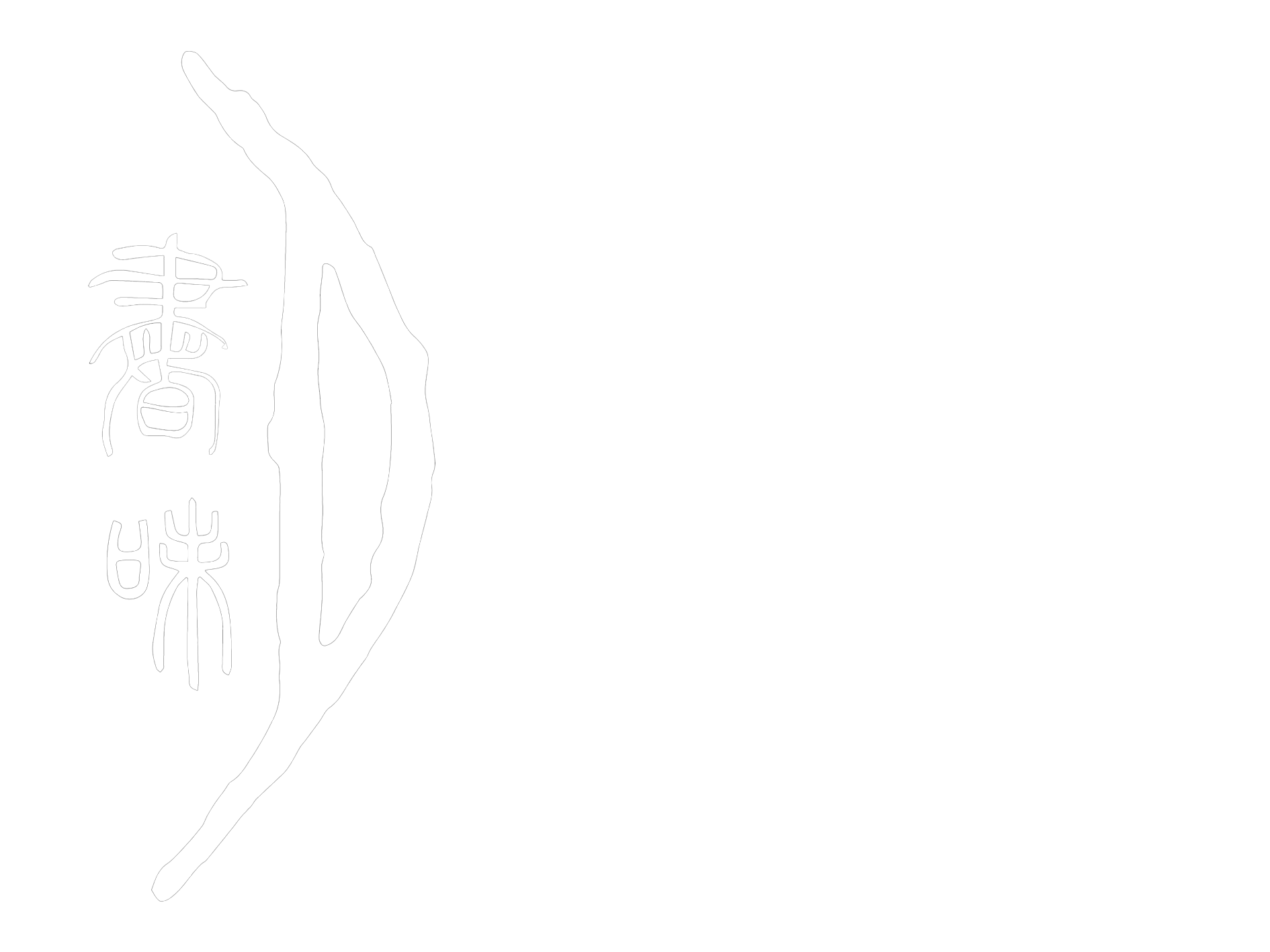
暂无评论
来做第一个评论的人吧!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