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民是以中国人的伊斯兰教(回教)社团为中心组成的社群,他们在香港历史上是与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裔及其他穆斯林社群不同的穆斯林。过去数十年来,有关香港回民的报导常常见诸内地报章,但长期以来香港社会在将印巴裔穆斯林看作是香港穆斯林的主体的同时,往往忽略了香港中国人穆斯林 传统上的回民 在香港社会的影响。虽然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回民在宗教实践、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与生活在香港的其他穆斯林群体显著不同,反而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沿海各大城市及内陆省份的回民社群之间往来非常密切。「香港回民口述历史」计划得到香港中国回教协会和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的鼎力支持,自2013年开始陆续对了解香港回民社群发展的历史见证人进行口述史访谈,并将其中一些口述史资料整理发表,以便社会大众了解和关注香港回民生活的变迁。
香港目前有二十多个穆斯林社团,但是由中国回民穆斯林组成的社团,主要是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香港中国回教协会、香港回教妇女会等组织。总体上,香港回民的历史与早期香港开埠的历史相关,最早一批回民主要是从广州、肇庆一带移居香港、并长久维持着与广州、肇庆等地回民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往来各地的回民客商和和从邻近地区迁居香港的回民陆续聚居在湾仔一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广州、肇庆的电车公司和电灯公司的职工,那时港岛中环、金钟一带还主要是英军的军营区。1917年,马瑞祺和锁春城两位香港回民先辈作为发起人,与脱胜初、金逸卿几位先生议定后,在夏高利律师帮助下申请注册成立了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并组成17人的委员会来筹办博爱社事务。随后,脱胜初先生将自己的一个铺面低价租给博爱社作为会址,从此香港回民有了第一个政府承认的属于华人的宗教聚礼的场所,每周聚礼人数有一百多人,但是十年后,至1927年博爱社才完成社团注册手续。1 1928年前后,任《南华早报》记者的回民萨兆经先生(1902-1944)也曾短时期出任教长,后来萨兆经与杨显荣、马庭植、马瑞祺、锁春城、马绍裘等一些有影响力的回民发起筹款,购买位于陈东里的一个旧货仓,将其改建为一幢三层楼的中华回教博爱社。1929年4月21日,位于陈东里七号永久社址的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 建成并正式开幕,这座木建筑物上层作为礼拜堂,下层为「义学堂」和办事处,由金逸卿阿訇担任第一任教长,马敬之先生任社长,开幕时有五百多人参加了当日的颂《古兰经》庆典仪式。根据当时博爱社的统计,那时全港的华人回民人口大约在430多人。2有了活动地点、建立了礼拜堂、积累一些公共财产之后,委员会决议聘请了专职阿訇在博爱社的礼拜堂带领做礼拜、为回民提供各类宗教服务,博爱社开始承担起服务湾仔回民社群的清真寺的职责。1939年,萨兆经等人出面聘请由香港到广州濠畔清真寺追随著名云南籍经师马玉龙(字瑞图)学习并已毕业「穿衣」的张广义阿訇(1911-2013)返回香港,出任博爱社教长并主持湾仔回民的日常宗教事务,直至张广义阿訇2013年归真,他一生为香港回民服务了近八十年。张阿訇回港任教长之后不久,另外一位在陕西、甘肃求学多年、毕业「穿衣」后回到香港的马达五阿訇也参与了主持回民宗教活动的事务。3 这样,作为香港历史上的第一个回民社团和礼拜堂,回民有了属于自己的宗教和社群活动中心,与集中在摩罗庙街清真寺的南亚裔穆斯林分开来做礼拜。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经过几年恢复,1949年香港又成立了中国回教协会即「回协」,整合了一批来自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回民代表人物来配合、协助博爱社的工作,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此后,博爱社和回协成为最重要的两个回民社团组织。1980年新建湾仔爱群道伊斯兰中心,即「爱群道清真寺」和重建九龙清真寺,这几座新建的清真寺逐渐成为新的穆斯林活动场所,成为回民穆斯林和其他印巴裔、东南亚等各地穆斯林做礼拜的清真寺。「九七回归」后,香港的中国籍回民穆斯林仍有三万多人,一方面,回民做礼拜的地点主要是爱群道清真寺,另一方面,大部分回民的家庭宗教仪式和社群活动还是到博爱社来举办。
徐锦辉先生1936年出生于香港,是土生土长的香港回民。长期以来,徐先生和他的父亲、兄弟都曾是中华回教博爱社的执行委员,1997年徐先生担任香港中国回教协会主席,2004年特区政府向徐锦辉颁授荣誉勋章,表彰他为香港社会所做的贡献。作为香港回民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之一,徐锦辉先生的口述历史是我们从了解香港回民社群生活变迁来认识香港社会的一份重要文献,以下即为我们过去三年间陆续完成的徐锦辉先生口述历史。
一、逃难的记忆
先说我们徐家的历史,我自己原本是姓哈的,过继给了徐家。两家都是回民,不过说「过
继」也不太确切,因为哈家兄弟姐妹多,我的生父比较穷,既烂赌又抽鸦片烟,没有办法养小孩,就把我卖给了徐家。那时候我还很小,这事的细节不太清楚。根据家谱,我爸爸即我的养父是徐家的第十传,叫做徐礼新,后来我续修《徐氏族谱》,情况才知道得多一点。我父亲是「礼」字辈,我是「锦」字辈。我弟弟徐锦强,才是我爸爸亲生子,这是后话。在徐家,我有两个母亲,都姓马。买我的这位养母叫做马梅初,买了我之后她又生了一个弟弟,取名徐锦文。「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从香港逃难到贵州独山的路上,我们被日军追赶上、截住了。因为我妈妈那时怀孕快生产了,走得慢,所以我父亲不得已将弟弟徐锦文交托给我的一位堂姐带着。走在前的堂姐一家到了独山之后,将弟弟锦文送给了当地的一家孤儿院,不料孤儿院又把锦文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领养,再也没有找到,那时徐锦文有五、六岁左右。我们开始逃难时,一路上都是我照顾着他的,所以后来我还是将他写入家谱。这是在逃难的路上发生的事,我爸爸徐礼新一听到我堂姐将弟弟徐锦文送孤儿院,又送了人,就急着去寻找弟弟,又将我留下来,委托给一起逃难的哈寿来照管。这样,我跟我爸爸就失散了。哈寿一家三口,他和太太、儿子一起逃难,我父亲给了他一点米、一罐炼乳,很少的东西,就将我托付给他,他儿子比我大很多,那时我还小,他就经常打我、欺负我。我们走到了贵州境内的一个村子,我打不过他,怕他这样天天打我,不想再跟着他们走下去,这里就有个阿婆愿意收留我,我也愿意留下来。当时身上没有一分钱,穿着一件毛线织的背心,哈寿一家把我留在那里,说「阿婆要收留你」,就走了。这位阿婆家,总吃那种用石膏做的豆腐,没有别的东西吃。我在1936年出生,逃难到贵州是1944年冬天,那一年刚八岁。记得总是下着雪,没有衣服穿,很冷。阿婆家有个儿子参加了游击队,不时会回家来,他有个老婆,但常不在家,他们没有孩子。晚上,阿婆家就把我放在家里的寿木棺材里睡觉,铺了禾秆(稻草)在寿棺的底层,我脱了衣服睡上去后,阿婆再用一块旧布给我盖住,上面再盖上长稻草,然后将棺材盖板盖住大部分,空出三分之一来透气,这样我可以比较暖和,就这样,过了一个冬天。这一家人后来我再没有见过了,也不知道这是在什么地方。阿婆的儿子不在家时,就是我和阿婆两婆孙在家里。他们跟我讲,屋顶上有个包袱,是阿婆儿子的小孩,夭折了,所以包着放在屋顶。阿婆的儿媳并不住在家里,住在另一个村子,她会不时来看看,她生了两个小孩都夭折了,所以阿婆非常疼惜我。
我爸爸同我失散之后,一路去到独山,在美军基地做劳工,是一般的散工。当他听说我被阿婆收养的消息,又连夜找回来,要把我赎回去。我爸爸找到阿婆,阿婆当然不舍得,那种情景历历在目!我爸爸给了他们钱,我当时随身的一件毛线背心,我在这家的「妈妈」、阿婆的儿媳,刚刚拆了准备用毛线给我织成新的毛衣,既然已经拆成线了,也就不还我了。就这样,身上空空荡荡的,我跟着爸爸离开了。我在阿婆家的时候有这样一件事记忆犹新,有一个夜晚,听见外面有「哐」、「哐」的敲锣声,我就走出屋外看,见到有一个灰色的、布包一样的东西在移动,前面有人在敲锣,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可是阿婆一家不准我去看这样的东西,他们说这是「走尸」、「运尸」,让我跑出屋看到了,阿婆非常愤怒,惩罚我,把我关到猪圈里跟母猪睡了一夜,这件事让我刻骨铭心。
我妈妈,也就是收养我的徐家妈妈,叫马梅初,她在逃难的路上到桂林时小产死了。那时她已经快要生了,到了桂林以后,白崇禧征用了粤桂铁路的火车,军人们用火车接载家眷亲戚逃难,非常拥挤,士兵们挤在火车顶上,上面还载运有军服之类。整列火车的中间一段车厢里、车顶上都挤满了难民,那么多人挤在车顶上,火车一过山洞要有是人站起身来,就会被撞下去,可是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要非常小心。我们徐家三个人同杨兆和一家一起逃难,杨兆和是杨义护的爸爸,杨家有两个大人、三个小孩。可是杨义护的大哥有一天在田埂上冲凉时淹死了,我们两家人今天一讲到这些,仍是很难过。香港逃出来的回民大家结伙一起走,沿路互相照顾,在火车顶上为了防止不小心掉下车去,几家人常常就将自己的身体跟装运的一捆捆军服绑在一起。至今,杨义护我们还常常回忆起一件事:有一天夜里,火车开行当中,突然间有个女人爬上了车顶,带着一个包袱,她看见我们就要跟着我们走。我们这些回民,有徐家、杨兆和家、萨爸爸家,我还有我一个姓徐的堂哥,大家一起走,最后也一起回到香港。那个女人上了火车以后,我们觉得她有些奇怪,我听到妈妈旁边有个人说,这个女人是个「以比利斯(魔鬼)」,大家要小心!不知是谁跟我妈妈讲,可能还是杨兆和妈妈讲的,「来,大家一起念经!」于是大家一路上就大声念《古兰经》,那个女人没念,她不是穆斯林。旁边有个军人知道这个女人同我们这一帮人不对路,觉得突然间另外一个女人塞进来也不好,就叫她下车,她却一直不肯走,她说:「我背着一个孩子,怎么行啊!」她打开她的包袱,里面真是个小孩子。军人赶她走,拿抢来出指着她,说:「你要是再不走,我就要开枪了!」她说:「好好,我走了!」就真的下车走了。这个军人也跟着我们一起逃,逃了一段路之后,日本人从后面追上来赶上了我们,在前面堵截,军人抢了我爸爸的衣裳裤子穿上,我爸爸个头不高,这个军人穿上我爸爸的一身衣服短一截,连个肚脐都露着,就跑了。
我们到了桂林,又一路从桂林往贵州方向走。路上我妈妈小产了,在贵州宜山(今为广西河池宜山县)归真了。她觉得肚子痛得厉害,叫我去给她买点药,但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能买到的药材中没有一味是安胎药。买不买呢?那时候我年纪小,不知道应该小心,结果我都不理,买了药回去,给妈妈煲药,没过多久,妈妈就小产了。那时我小,又不懂;当时候爸爸并不在身边,只好拿些东西盖住这些血块,小婴儿都看到,妈妈就这样去世了。后来杨兆和,即杨义护的爸爸、我爸爸、姓徐的三哥、萨爸爸,我们几个用一张布包住就地葬了我妈妈。我看到小产夭折的弟弟,脐带都还连在身上,我太小了,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那一列火车上最多回民穆斯林,有哈生即哈耀恩和他的几个儿子、他太太、还有他妈妈;有我的堂姐和她的丈夫,此外还有一个在香港的回民穆斯林中很有名的叫「十哥」的,也是姓哈;还有一位是哈奇伟的爸爸哈文龙先生,他现在九十几岁了,还健在。曾经有一起逃难的人从火车顶上掉下来摔死的,大家见到了,于是就有一个人把自己绑在头一节车厢上一个备用的大轮子上,没想到轮子也掉下了车,这个人跟着掉下摔死了。那时,一起逃难的回民大家都能够相互照顾,所以我们有很好的关系。进入贵州后雾大得看不见四周,有时大家要一起走路,大雾中见不到人,只有一边走、一边大声喊着别人的名字,比如姓哈的有十一姐、六哥,就大喊「十一姐」、「六哥」,大家还用裹脚带串成一串,当时大家的想法,就是往内地走,尽量上去到独山,总之没有日本仔的地方就好了、哪里没有日本人就去哪里。后来日本人追上来赶过我们往前去了。我也看见过日本人把哭个不停小孩子,用刀挑起来用枪打死,真的!血溅下来,洒了我一脸,味道很臭。这个你真是不相信的!真是这样的!天冷下雪,我们用棉花包着脚,没有饭吃,我们找到一块生牛皮连着牛毛的,把牛皮跟野菜一起煮着吃,吃上三、四天。雪是白色的、棉花也是白色的,火星落到脚上棉花烧着了,把脚皮也烧焦了,当时的情景……(长时间沉默)。就这样,大家一直走,走到独山的美军基地。很多回民穆斯林都是去到独山为止了,因为有的人会英文,帮了美国人做事,介绍大家去做工,我爸爸就做了一个普通的杂工,生活能够维持。和平之后,我们大家都一起回来,在那里住了多长时间,已经不记得,当时太小了,杨义护的大哥,就是在田埂边冲凉时跌到水里没人看见,淹死了。稻田收割之后田里还是水,看不清。小孩们在冲凉,我爸爸、他爸爸等一帮人都在哪里的,玩着玩着,就不见人了,也没注意看住他,因为还要照顾其他的孩子,杨礼护、现在我们香港中国回教协会的会计师杨义护,还有他们的妹妹杨小梅,我们都很伤心。后来我们能有那么好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曾经一起逃难、一起回来。
二、香港的回民清真饮食业
为什么大家会一起逃难?抗战之前,大家都住在湾仔天乐里,我爸爸徐礼新开了一间名叫「新新」的餐馆,我妈妈,即我的养母马梅初,她出名有本事,做的菜非常有特色。和平以后大家逃难返回,我爸爸又开了「新昌鸡鸭」摊檔。当时,我们家以卖腊味为特色,主要是腊羊肠、腊鸭、腊野味、挂炉等等。我们当时卖的、现在所谓的「挂炉」,过去叫「挂烧」,用的工具很特别,用很大的叉子,我从小就跟爸爸学习如何做,所以我也很在行。我的子女现在常常跟我说:「老豆,很久没有吃这些了!」现在都找不到那样的叉子了。很可惜,现在大家都不做清真饮食这一行了。我爸爸也把煮咖喱的手艺传给了我,后来我还教过不少人,二十年前我还在《大公报》工作的时候,还教过一个亲戚的女儿做咖喱,她后来到澳洲开餐馆,以卖咖喱为主,一直到她退休都是靠我教给她的那几样手艺,我教过的徒弟也不少了。我们先开了「新昌清真餐馆」,当时很有名,后来我爸爸开了一个「友兰餐室」,地点在今天还能见到的「同德大押」隔壁。我爸爸教过一个姓萨的徒弟,叫做「五仔」,「挂炉鸭」的功夫我爸爸就传给了他,后来「五仔」移民去了英国,在英国唐人街很有名,五仔脾气暴躁,非常容易发火,可是他一直非常敬重我爸爸。
今天湾仔鹅颈桥街市「清真惠记」的前身,就是「烧挂炉鸭」,在陈东里对面,原来是卖烧鸭的大排档,后来才搬进街市中。有关香港清真饮食的过去,既没有人提过,也没有人写过。我家就一直跟清真餐馆行业有关系。现在的爱群道伊斯兰中心五楼的餐厅,最初是我来经营的,这其中有另外一件事。以前香港伊斯兰联会(IU)负责饮食管理的人,是个马来西亚裔的女士,是位护士,叫努比亚哈森。我经营伊斯兰中心餐厅的时候,我做鸡杂是用新鲜的鸡杂,外面吃不到,因为我的餐馆是用自己的配料,选材料也非常严格,生意不错。可是我接手餐厅经营的时候,大家没有将合同的细节谈清楚,有一年斋月,努比亚哈森要求斋月间停止干生意,所以斋月期间我们没有经营;开斋以后,我本来计划餐厅可以重开了,可是她要求我再停,这样我就不能维持了,只好关闭了伊斯兰中心的这间餐厅。八十年代初我还经营过另一间餐厅,是博爱社的房产,在利景酒店前路口,位于二楼。我经营这间清真餐厅专做「清真私房菜」,算是「中华回教博爱社」的餐厅,很出名的。我自己并没有亲自做大厨,请一些熟悉的师傅帮手,自己知道如何经营,我们家开餐馆已经很多年了,加上自己在报馆有一些人脉,接到不少生意。这个餐馆办的很成功,伊斯兰中心建好之后,餐厅需要找人来经营,所以我也就关了博爱社的「清真私房菜」餐厅,转到伊斯兰中心餐厅去,那时我的子女们都要来帮忙,做些收银之类的工作,那时候,我爸爸还在开「友兰餐室」。清真食品行业,今天还在经营的「马家庄清真饭店」也是我们一起逃难,一起回来的。我爸爸同他们一家也非常熟,他们家长辈,我们也是叫「爷爷」,后辈就不熟了。我爸爸经营「友兰」的同时间,当时还有一间也很出名清真馆,叫做「文强冰室」,是杨志英家开的,我们也在鹅颈桥街市「清真惠记」楼上开过食肆,生意很好,卖开了名气。
当年我们卖烧鸭不像现在,我们是不放味精的。我爸爸教我们用的配料、份量,都是用糖,也不用花椒、八角。为什么我爸爸会经营清真餐馆呢?他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照排行叫他「七叔」、「七伯」,早年他是个行船做水手,在船上学过煮餐,在船上做过厨师。他应该不是在香港出生的,归真时是100岁左右。我们逃难往桂林走的时候,他在桂林也做过小贩,卖清真小食品油香、眼镜酥之类,他还会做一种很特别的点心「糖炸鸡蛋」,鸡蛋用糖发,油炸,入口即融。做油香我父亲也非常拿手,他还会做一种油饼,也是中空、油炸,放虾米;另外一种炸麻花,在国内也吃过,香港现在也没有了,技艺失传了。我爸爸是很能干,这些都不是家传,是他自己学来的,到我这辈就成了家传。战后回来,我们家就住在一个唐楼里,有骑楼,我住的那个地方,里面住了七伙人,我睡的是一张床板、两张桥凳,早上收起来,晚上才打开,工作坊是它,睡觉也是它。我们家做的腊味,叫做「清真羊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做出来。我们做腊味是先将牛肉切细,以盐、酱油、糖等佐料来调味,再将肉灌入羊肠中。最难的工序是做肠衣,我们用筷子的四方形尾部这一头,来将羊肠的内壁刮干净,这样肠衣就是通透的了,有时肠衣一天用不完,得用盐腌住第二天洗净继续灌。羊肠衣做好后,往里面填牛肉、牛板膘。牛板膘中最好的部分,叫做「牛胸尖」,以前广州的清真餐馆还有一道菜叫「炒牛胸尖」,你们没有吃过了。「牛胸尖」是牛胸脯上的一层油膜,可切成细粒、跟牛肉拌匀,用漏斗填入羊肠中,然后将一条水草撕成四份做线,绑住羊肠的头尾以防酱油、糖等调料溢出。一根腊肠,中间要分扎成两三寸长的几段、用水草绑住。肠里面有水的话会胀起来,所以还要用大头针戳破它,将水逼出来,最后挂到天台的天蓬上晾干。腊羊肠冬天才做,以风吹干或者用火焙都可以。清真羊腊肠至今在广州还有人做的,香港就见不到了。另外我们也做腊鸭,鸭子是内地来的,我们要判断鸭子可以留多少时间、有没有染上瘟疫,只要握住鸭子的嘴、脚看,就知道这只鸭健不健康。如果突发了鸡鸭瘟,就要「赶刀」,有一次我们一天就宰了一百多只。现在没有活鸭,辨别鸭是否新鲜,就要看血色。血红色就不新鲜了,冰鲜鸡、鸭都是,如果骨头是黑色,那是已经宰了很久的了。腊鸭先用粗盐揉一遍,再用大桶腌一晚,第二天早上起出用清水冲洗去盐。如果不想吃得太咸,可在一盆温水中浸泡15-20分钟后起出铺在筲箕上、背脊朝上晾好,将大腿骨折断、压平,待北风来吹干了,再翻转过来以内肚朝上晒一段时间,得用白胡椒撒上,苍蝇就不会来。很多人还不知道用白胡椒粉赶苍蝇的方法,晒鱼干也一样。吹、晒干之后,将鸭子装入瓮缸中密封两天后提出来晾干,香到不得了。另外,鸭髀的做法是用盐腌上一夜,次早铺在筲箕中晒干,比较容易处理。有时国内来得一批便宜的鸡鸭,就多买存货,进货量并不固定,那时即使养在档口也没有什么禽流感之类。战后至五十、六十年代香港清真食品的供应,「泉昌」号就一直是卖鸡鸭的,「泉昌」号也供应牛肉,就供给「泉秀」餐馆,他们是两兄弟,在跑马地;「联兴号」的老板姓马、「厚安号」姓丁,都卖牛肉。当时的牛肉也是由广州定点供应香港,运到才宰,所以杨明钧家就负责买牛、宰牛,我们吃牛肉就是靠他们,屠宰场在西环。刘中这一家在香港也以做腊肠出名、所以除了「泉昌」卖清真腊肠,有一些茶楼也在卖。在香港的清真餐饮行业中,刘中的哥哥也在香港做餐馆,手艺不错。当时最典型的中式餐馆,每张枱下都放个痰罐,今天看来就觉得有趣。我们徐家主打「白切羊肠」、「肥大油鸭」,那时广州羊肠师傅是我们的亲戚。在那个时代,烧腊是跳着沿街叫卖的,送上门,切一段、切一块,这样来卖。
战后十多年间,香港回民穆斯林中虽然有不少人做文员、做律师楼的,比如脱志贤就是在律师楼,但是回民主要从事的还是在饮食行业、电车公司,也有在兵房煮咖喱的。我记得过去开斋、过「古尔邦」节,我爸爸就到「大庙」即些利街摩罗庙清真寺去煮咖喱饭给大家吃,煮咖喱的炉子上下两层都烧炭,虽然各有自己的活动中心,回民和印巴穆斯林来往也很多。抗战时期,印巴裔穆斯林没有逃难,日本人占领了香港之后,很多印巴穆斯林用澳门的关系躲到澳门清真寺那边去了。所以,「抗战」时期香港回民一起走难的人,主要是哈家、徐家、杨家、脱家等等,我觉得那时大家比较「迷信」,比如我妈妈死之前她就说,从火车顶上面往车下看,看路两边全都是「以比利斯(魔鬼)」在跳舞。八十年代,沙特有个卖石油的王子要去内地考察、计划买一个矿石场,我陪同跟他一起去,找到了我妈妈死的地方,在那里做一个「堵啊」,但那是个大体的位置,具体的地点都记不清了,我只能在跑马地回教坟场为她立个石碑做纪念。
三、五十年代以来的生活变化与记者生涯
过去回协同博爱社实际上是同一个组织,例如1975年1月1日出版的博爱社简讯可以看到,回协与博爱社都是同一批人,那时我们一家三人都在博爱社做执行委员,徐礼新是我爸爸,徐锦华是我弟弟,杨兆和是杨义护的爸爸,我们都是曾经一起走难的。七十年代香港成立六宗教联合会(佛教、天主教、孔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道教),最初代表大会的安排,就是回协、博爱社双方同时参加、由博爱社的人做代表,后来双边有些分歧,由博爱社来代表了。1972年,香港回民第一次组团去北京访问,参观东四牌楼清真寺,我爸爸还拍了一张手捧东四清真寺珍藏的大本子的《古兰经》照片,后来刊登在博爱社社刊上。那次去的人不少,脱维善先生、萨智生先生、傅爱贤先生都去了,我当年是秘书。当时陈广贤阿訇是东四清真寺的伊玛目,我们与民宗局的人本来就认识的,后来又加强了联系,不过这是第一次正式的拜访。返回香港之后,当时任博爱社主席的脱维善先生又再去了北京一次。为回民、为「教门」做事,脱先生是非常积极的,他是第一个搞清洁公司的人,深圳刚刚开放时,他就到深圳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后来他成为全国政协委员。随后很多年,脱维善先生都代表回民参加历届的六宗教座谈会,在六宗教联合会中也做了很多事。由于回协一开始就与博爱社一起参与了六宗教联合会的活动,同时我又是博爱社的执行委员和干事,我也就参加了六宗教联合会的秘书处。考虑七十年代的政治气候,脱维善先生与我们商量,回协作为爱国进步组织,还是与博爱社分开、不将回协的事务带入博爱社中,因为回协是香港第一个挂五星红旗的回民社团,自成立起每年举行国庆宴会,当时《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等人都来参加,记得特别是1961年的国庆宴会,巴基斯坦国家银行行长等很多外籍穆斯林的领袖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从当时的情况考虑,中国人的伊斯兰教组织要有分工,博爱社是纯宗教性团体,回协那时候由《大公报》的回民白学修先生负责,宣传爱国、爱教、爱港,也向香港和海外介绍国内情况、组织回民返回内地参观,在当时的香港和海外华人穆斯林团体中,回协是非常活跃的。七十年代以来,回民在宗教上对外联系的窗口就是与参加「香港六宗教联会」,大家都认识我,例如新年团拜等活动,就是我在联会秘书处发起的。我们伊斯兰教除了拜真主之外,不用「拜」这个字,所以把「团拜」的字眼改为「团贺」,沿用到现在。
说到我个人的工作和社会活动,虽然我担任回协负责人的时间很长,做事还是以博爱社为主,原因是自1959年到《大公报》社工作,我一直积极参与回民社团的事务。我刚到《大公报》社工作时,社长马廷栋先生也是回民,他是有名的报人,在报业中拿过国际奖。《大公报》的白学修先生那时任回协主席,他是马廷栋先生的舅父,都是从广州来的。所以当时有人就说,回协是极左的组织,确实,在五、六十年代香港回民与广州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白学修先生在省港大罢工时就是回民参与省港大罢工的工会领袖,刘就也是回民中的重要领导人,而马兆雄先生又是白学修的舅舅、他跟脱志贤先生又是同事,大家还一起逃过难;另外一个是罗学新,他们也都是回协、博爱社两边都是活跃的活动分子。1972年开始,我从《大公报》脱产,帮助霍英东做体育方面的工作,身兼多职,虽然很辛苦,但是也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社会层面的事。在博爱社方面,脱维善后来参加全国政协委员到四川考察的活动,在途中心脏病发作归真,哈耀恩先生继任博爱社主席,哈先生也是和我们一起走过难的,我自己又是哈家生的人,我们认兄弟,我就叫他「六哥」。我父亲徐礼新有个弟弟徐礼仲,他的女儿嫁给哈新,就是我的堂姐,哈新还有三个兄弟,其中一个就是六哥哈耀恩,所以,香港回民这些姓氏,绕来绕去都是亲戚。在我脱产搞体育工作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还要抽时间来帮哈耀恩先生处理一些博爱社的事情,直到哈耀恩归真之后,脱志贤先生接替他任主席。
为什么我会到《大公报》去做记者?这要从之前上中学的事说起。香港有一些名人像何志平、石辉,都是我在拔萃中学的同学。本来我在伊利沙白中学上学,1956年我读中四,那时我的特长是体育,短跑速度很快,当时香港有个全港田径公开赛和学界田径赛,我是100米、400米短跑的冠军。我在学界田径赛中100米跑出了11秒的成绩,因此成为国内「统战」工作的对象。那时我每年回广州比赛都是用假名的、经过澳门回去,是通过香岛中学的一位老师联系的。台湾方面也有人在学校中做学生工作的,我记得伊利沙白中学有一位姓陈的老师是体育主任,叫我去参加台湾的比赛,只要见到人就给钱了,但是因为我总是返回大陆去比赛,就没有跟他们联系。那是1954、1955、1956这几年间的事。1956年澳洲墨尔本要举办奥运会,中国在北京举办奥林匹克选拔赛,我去北京参加了短跑选拔赛,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由于这一届奥运会,要跟台湾争奥运会会籍的问题,中国最后退出了奥运会。不过当时我在短跑选拔赛中夺冠的事轰动了香港,台湾方面又在积极让我们参加台湾方主办的运动会和选拔赛,伊利沙白中学又是港英政府的学校,所以我从北京回到香港后,伊丽莎白中学就不让我继续念书了,那时香港的政治环境是非常抗拒大陆的。不同的是,拔萃中学男校是圣公会的学校,属英国人中最亲中的,拔萃中学校长施玉麒是一位教圣经的牧师,所以我当时就有疑问,为什么香港学界最先唱国歌的是拔萃男校而不是那些爱国学校?当时的爱国学校主要有香岛、培侨、中华中学、劳工子弟学校等。所以,有好多穆斯林的子弟,有名的比如马宝华、当法官的石辉等人,从那时开始都纷纷入了拔萃。拔萃男校的体育主任姓郭,也是很出名的,后来做了校长,我从伊利沙白中学退学后,他就让我到拔萃男校去。到了拔萃恢复学习后,很多英国人老师来给我补课,班主任是个英国女士,她丈夫就是英国舰队的舰长,她让我放学后就跟她回家去补习,她有个儿子是圣乔治学校的学生,年纪跟我相仿,我放学后就到她家吃饭、补课、问她儿子问题。那段时间我有个体会,大家有一种迫切的心情,非常关心中国国内的情况,感觉是这究竟是不是传奇。另有一样好笑的事,我考会考国语课,老师姓徐又同我很要好,问我很多有关国内情况的问题。会考他来主考,我想都跟他很熟了,以为没有问题,结果他给我不及格!那几年中,自己心中最关切的是国内情况如何,自己的爱国心是自然而然就产生出来的,这三年对我是很重要的。
最不幸的是,中学毕业时校长推荐我去英国学习水翼船,搞航运。有几个同学当年就去了日本,但是我自己家庭情况不允许。由于我是我爸爸收养的,我同他商量,那时他正在经营「新昌鸡鸭」,他告诉我如果我真有心去,他就去借钱供我念书。战后我爸爸再婚了,我弟弟才4岁,我妈妈那年39岁,父亲很辛苦,自己是不忍心的,所以就放弃了。同我一起被推荐到英国读书的还有一个姓张的回民同学,回来后成为澳门娱乐公司船队的负责人,水翼船是霍震霆去订的。我没有去成英国,1959年中学一毕业就急于找个工作。当年认识一个爱尔兰籍的警员,他后来是国际刑警反毒警司,也是在香港跑短跑的,我的花名叫「非洲」,是跑得快的意思,他的花名叫做「白皮猪」,名字叫麦马汉。他知道我不去英国,就介绍我去惩教署工作。我不想考帮办,在惩教署也有很多穆斯林,大多是伊斯兰国家来的,还有个爱尔兰人,叫 E. K. 嘉道理,也是我们读书时候的校友,他让我不用考试,直接去见头头,甚至让我去验身之后就可以上班。那时做惩教署还配备皮鞭,后来我回去跟爸爸说,已经通知验身了,但还是决定不去当差,原因主要是政治审查我肯定通不过。我去了北京,连学校都没有得读了,如何能过这一关呢?父亲也不主张我到惩教署工作,因为我姓哈的兄弟已经在纪律部队,他不想我们三个兄弟都做纪律部队的人。另外,他认为我个性也不适合当差,就希望我试试报馆,回民都认识马廷栋。当时左派的政治门坎很高,我就找到回协主席白鹤修先生,跟他提希望去报馆做事,等了一段时间,突然《大公报》通知我去面试,星期五才去报馆见面,星期一就要我去上班了,这样我就入了《大公报》,那是1959年3月11日。既然我是搞体育的, 报社就派我做体育版记者,但有师傅带着。马廷栋知道我当年因去北京被迫害的情况,我是回民「榜爹仔(Panthay)」,短跑出名了以后被学校开除、入了拔萃,而且我又同何东的曾孙、何世礼的儿子他们这一帮人关系好,比如莫闻兰、莫天锡、莫天福等,他们对新中国都不反感的,拔萃毕业生日后很多在香港政府工作,跟他们打交道也方便。另外《大公报》方面也有很多原因,我做体育新闻之后知道,中国当时未与泰国建交,泰国的事务是通过社长费彝民联络,随后我们负责了采访了在泰国的举办的国际羽毛球公开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太太是我在伊利莎白中学时的同学,她家庭条件很好,有14个兄弟姐妹,她排行十三,她父亲在政府和教会中都很有威信,中英文都很好,中学时她家住在跑马地崇正会,那时每天上学我们都要搭电车由跑马地到西环,就认识了。后来我去北京参赛返回后,就一直有来往,1959年我进了大公报,1960年她也毕业了。两个人谈恋爱时,考虑到经济问题,我放弃了去英国,她毕业后也急着想找份工作,所以我在《大公报》向马廷栋提出来,他先是反对的,认为两个人不一定要在一起工作。她只好去考护士,后来我找了另一个更加资深的杨力樵先生,杨先生接受了她,马廷栋于是要她来面试。当时没有多少读书毕业的人来报馆工作,那时入了《大公报》就算是激进的了。她进入《大公报》以后,报社重点培养她,也送她进大陆学习、反英抗暴也被抓过。我们两个都在报社做到退休的,很怀念报社,当然工作也很辛苦。记得刚刚工作时,工资是每月180元,如果当时进了惩教署月薪是400元,还有16元的服装费。我们是1961年结婚的,婚后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是每月560元,到了生了孩子的时候,月薪加起来是每月640元,那是1962-1963年前后,那时我们花90元请了一个工人、120元付了房租。1964年我开始升职为正式的体育记者,工资也涨到400元。
1956年奥运会后,台湾是国际奥委会的会员,北京就撤出了国际奥委会。采访泰国国际羽毛球公开赛是我新闻工作的开始。当时香港的羽毛球队在泰国很有影响,我们随队到达泰国后获得了高规格的接待。在记者招待会上,《南华早报》一位记者问了泰国的国防部长他威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当时提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帮他解围,他威很高兴,专门给我一个单独采访他的机会,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后来中泰建交的时候,他带了一个代表团去北京访问,还来到香港。中国与马来西亚建交以后,他们的体育部长是位穆斯林,后来又出任国防部长,我们也有往来。那时霍英东先生出席过很多与领事们联系的场合,所以霍英东出面联络,我帮霍英东先生做一些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地位的和体育外交的工作,康有为的侄子康立新先生也一起来做这件事。
1972年我被借调去帮霍英东先生做事,那时是《大公报》的体育记者,也算是出名的体育记者了,我就一直负责参与接待中国的第一支乒乓球队的外访,与徐寅生、查济民他们很熟。中国乒乓球队到香港来比赛,我们常常都在一起,那是尼克松访华时期,「乒乓外交」是很出名的了;后来1974、1975年间,体委派羽毛球运动员来香港比赛,要见报做宣传,霍英东来负责,我那时任香港羽毛球总会的秘书。那几年我工作太忙的时候,连子女都来帮忙,很多事情都要向港英政府申请。后来我参加了香港帆船协会,罗鸿那时候是负责人。也是在1974、1975年左右,北京派李君夏来香港,我们曾是伊利沙白的同学,也在一起工作。早在1967年「反英抗暴」时期,新华社领导我们全香港的左派机构,分成四组,我负责一个组,文汇报的张文峰、周正民都是我这个组的,我太太也在我这组,她负责报馆之间的联络。那时港英政府逮捕了很多记者,北京提出抗议,烧了英国大使馆,事情搞得很大,因此,港英政府这边对我很不满。那时我们的工作小组有分工配合,李君夏负责翻译,把所有中文报纸的社论及评论翻译为英文,作为Chinese comments给各大英文报纸刊登。这样,我们可以掌握到香港市民重视的那些新闻事件。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又很受政府和各大报的欢迎,凡是我们提供的新闻稿,香港政府新闻处每天必读。我逐步认识到我们需要做些选择,那时的时事新闻主要从《明报》来,也有很多其他报纸,我们就把大家关心的问题都收集起来。《南华早报》的社评是陈大维负责,他有什么社论,写了常常来叫我看,有没有什么意见。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段时期,我自己也写一些报导中国现状的文章发在各大报的中国版,见报的文章很多,主要讲讲中国国内的事。
除了这些工作以外,我当时还兼职做翻译,也是出于生活上的经济压力。我们有两孩子,儿子和女儿都先后出国念书,女儿去瑞士读酒店管理,儿子去了英国。当时我在《大公报》人工远远不够。女儿中学毕业后跟我讲想要去瑞士读书,如果我不支持就不去了,我一口答应下来,但是心中没有底,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她一年需要学费两万多元。有一次,我同霍英东先生在谈外出活动的问题时,就向他提出来女儿要去读书的事,跟他说,每年亚洲只有20个名额,我女儿考取了,不容易。霍英东同他的秘书讲,「你明天给他办汇票!」一年学费两万多港币,霍英东吩咐秘书林先生买一张汇票,足够付一年的学费。我同霍震霆先生讲,我一时还不了,得要分三次还;霍震霆说不用还,不过三年后,我还是将钱还了。我爸爸归真时,霍英东先生带了全班人马来送葬,当时我叫我女儿过来,要多谢霍伯伯陪他们吃饭、送行。我女儿说:「这事到了此时她才知道」。很多人都以为我跟霍先生一起工作这么多年,他会给我很多钱,但是没有。1974年我同霍英东参加了在伊朗举办的第一届亚洲运动会,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我非常敬重霍英东先生,他有爱国心。话说回来,在《大公报》时,我每天要做三份工作,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家里的经济问题。在《大公报》工作、后来同时又在《南华早报》当译员和体育记者。后来报馆的领导换成李侠文,接替费老当了社长,他曾经跟其他同事说过,「徐锦辉不知道的事没有了」,那时《大公报》还出《新晚报》、《体育报》;此外,我还负责将英文报章的体育新闻及足球花絮译成中文。每天工作日程就这样:中午12点到「南早」上班,写、翻译社评,做到大约下午两点半左右;三点钟回到家中伺候父亲,我父亲后来年纪大了,半身不遂,要每天给他擦洗身子。下午四点,要去到东区法院「收料」,作为《大公报》、《新晚报》的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因为当天的案件、新闻到那时会发布出来,最后才返回吃晚饭。晚七点半再返回《大公报》馆写稿,至十一点。就这样,做了十年。就在这段时间,我还兼职负责回协、博爱社的事,不过也是有时间才去处理一些事务,因为工作太忙,回协、博爱社那两边常常都找不见我,成了「无影侠」。不过那时心情非常好,很开心做这些事情。我儿子中学毕业后先在《南华早报》做一段时期的发行工作,我女儿先去瑞士读书,等女儿快回来来,才送儿子去英国念书。羽智云那那时是伊斯兰中学的副校长,他曾问我儿子想不想出国念书,儿子说「想!」我们将在香港仔正在供的一间屋卖掉,也只刚刚凑够他一年的学费,送他出国。我们夫妻两就在文汇报的一间套房来住,将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间房内,一开门,就只能上床。女儿从瑞士回来度假看到这种情况就哭了,说不读了,那时刚刚她读了一年书,她向学校申请休学,工作了一年,自己赚了钱又继续读书,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一家人始终感情很深。
在回民中,马达五阿訇是个很热心的人,他参与湾仔伊斯兰中心的很多活动,所以伊斯兰中心将图书馆命名为「马达五图书馆」。伊斯兰中心和湾仔清真寺都在同一座楼,1981年湾仔爱群道清真寺暨伊斯兰中心建成开幕后,这座楼主要由回教信托基金来管理,但是博爱社并没加入在1970年成立、向香港政府注册的「香港伊斯兰信托基金会」,当时主要的考虑是法律的要求,如果加入这个基金会,就要进行屋契登记、要交钱,那样的话,就等于将回民的中华回教博爱社几代人积累起来的财产交给了基金会。2015年,香港伊斯兰信托基金(The Incorporated Trustees of the Islamic Community Fund of Hong Kong)出版《香港穆斯林社群》(Muslim Community in Hong Kong),当中没有提到香港的回民穆斯林(the Chinese Muslim),原因就是信托基金成立时回民没有加入,信托基金也就不理博爱社了。回归之后,信托基金又邀请博爱社参加,当时的主席脱志贤先生认为,既然已经回归了,也就没有再加入的必要了。
注译
1 民国十九年中华回教博爱社宣传部〈致旅港本 教 同 仁 公 函 〉 , 载 《 穆 士 林 》 , 第 三 刊(1931),页58-60;《中华回教博爱社社刊》,1975年元旦号,第二版。
2 《天方学理》,第8期,1929年5月,页8;《穆士林》,第一刊(1930),页6-17。3 2014年7月10日,对萨智生先生的访谈;2014年10月23日,对张大恩先生的访谈,并见中华回教博爱社出版,《中华回教博爱社社刊》(香港:中华回敎博爱社,1959),页5902-5903。
(书味根据《田野与文献》第八十四期录入,原标题:“香港回民口述史(一):徐锦辉先生访谈”。马健雄在2014至2016年访谈并记录整理,主要访谈地点为伊斯兰中心马达五图书馆。作者供职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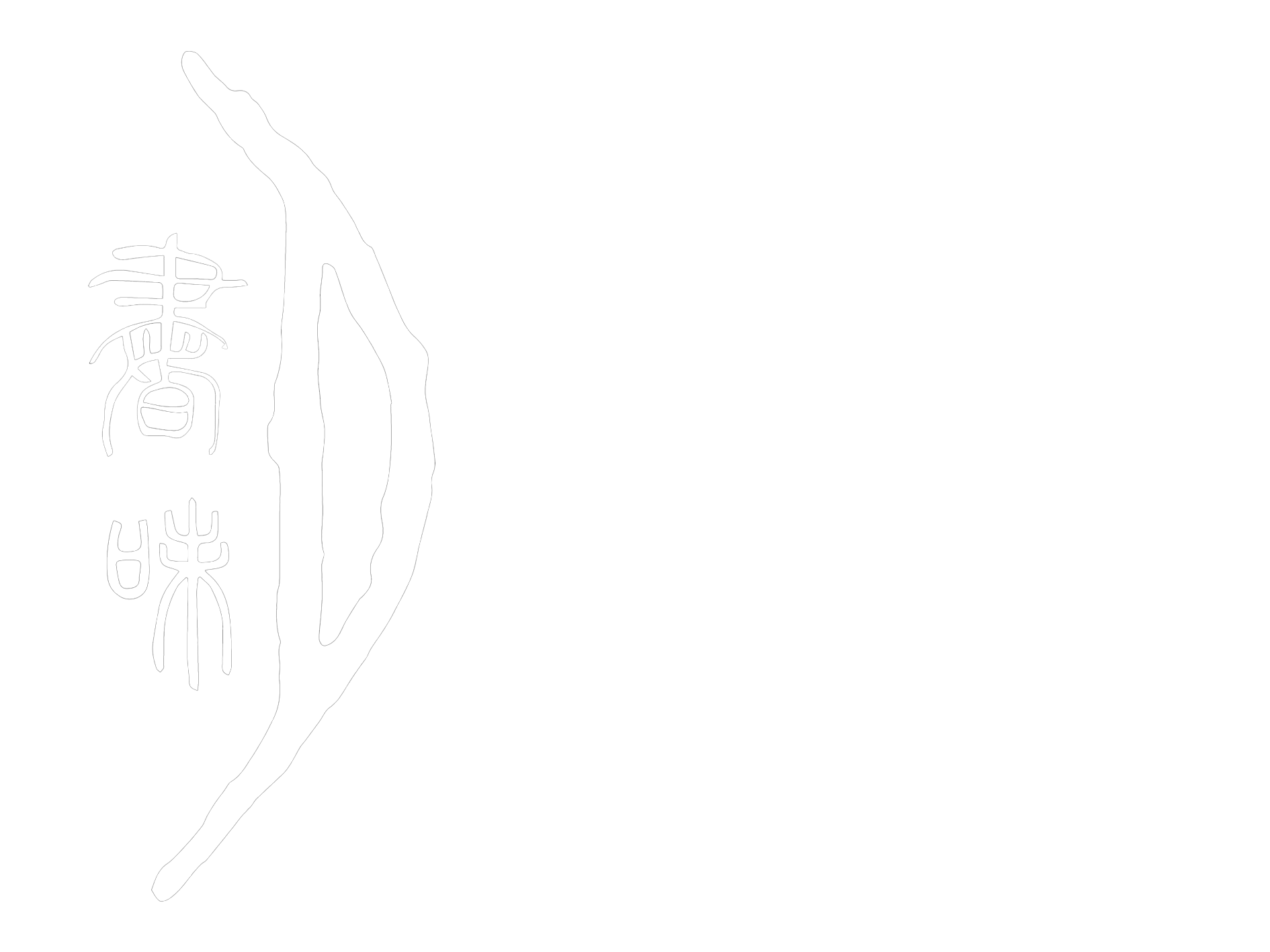
暂无评论
来做第一个评论的人吧!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