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二年(清朝同治元年)春天,在陕西省中部渭水盆地的某个村落中,爆发了伊斯兰回民所组织的民间武装集团与汉人集团之间的冲突。汉人发动称之为「洗回」的屠杀;回民则以受「洗回」逼迫为由,煽动群众起事。冲突最后演变成叛乱,这场叛乱瞬间蔓延到包含新疆在内的整个清朝西北地区;换言之,就是波及到我们蒙古人现今称为「伊斯兰中国」的地区。
叛乱开始之初,在我故乡鄂尔多斯高原上的蒙古各部,比其他地方都更早卷入战祸之中。壮年男子奔赴战场,老人小孩纷纷避难。对于这段过往,蒙古人至今仍历历在目般不断传述着。和回乱有关的蒙古人,在身为被害者的同时,也算是「加害者」的一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蒙古身为统治清朝的满洲人盟友,因此从穆斯林的角度来看,至少也是属于「镇压者」的行列。
事实上,清朝政府并没有办法发动昔日强悍的满洲、蒙古铁骑来镇压这场叛乱;因为清朝在先前的太平天国之乱中,已经陷入疲敝的状态。这时候登场的,是像左宗棠这样的汉人能者。被称为「中兴名臣」的左宗棠,一方面展开以「善后」之名包装的无情屠杀;另一方面也设法分化回民内部,从回民阵营中找出愿为清朝效力的人士。就后者而言,马占鳌(一八三○—一八八六)就是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马占鳌为了保存穆斯林势力而积极行动,甚至对一起参加叛乱的部分同伴挥舞屠刀,结果在清朝的西北部,诞生了由穆斯林军人所率领的强大集团。原本只是缓慢凝聚的回民,因为叛乱与镇压的经历,反而坚定地团结在一起。回乱对回民来说,无疑是一条凝聚认同的道路。
叛乱后的穆斯林军人,在清朝政府内部获得了与蒙古几近同等的政治地位。
不久之后,清朝瓦解。大家都无异议认为,西北回乱是促使满洲人王朝衰弱的原因之一。蒙古人趁着清朝灭亡的契机,开始为了完全独立而奔走。可是随着时间流逝,原本暂作壁上观的穆斯林军人转为中华民国效忠,扮演起以武力抑制蒙古人独立运动的角色——也就是说,为一直以来压抑他们的汉人效犬马之劳。
到底为什么蒙古与穆斯林的政治立场,会如此迥然相异?
要探寻这点,有必要回顾清朝时代的回乱,对蒙古人究竟代表着什么意义。
从外部展开的观点——蒙古史还是中国史?
在谈论历史时,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观点。
一九四九年,受到美国人类学者提出的涵化论与同化论影响,历史学者魏复古(Karl August Wittfogel)以契丹人的辽王朝为例,提出了「征服王朝理论」。此后,这个理论在日本历史学界引发了形形色色的议论;也有人将征服王朝理论投影到日本历史上,提出了「骑马民族征服王朝说」。
在各种说法中,包含蒙古在内的北亚各民族历史,其历史究竟是独立存在,还是应该算成中国史的一部分,成了讨论不休的焦点之一。这种议论不只存在于学界,也和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彼此关联。我称这样的理解方式是「从外部展开的观点」。
一九五一年,村上正二撰写了一篇名为〈蒙古史研究之动向〉的论文。简单归纳他的主张,大致如下。
「蒙古史研究的基本课题」之一,就是北方的游牧社会对南方农耕社会树立统治权,也就是所谓征服王朝的问题。要究明这个问题,首先就必须解明北方游牧社会的内涵,也就是「游牧是什么」。一直以来,「狩猎—游牧—农耕」这样的发展阶段说是许多人深信不移的,但是不管游牧社会或农耕社会,都不是对应历史发展阶段、立基于生产技术面的产物;相反地,它们是包含全体的统合概念,也就是社会类型的概念。因此在解释亚洲全体社会发展的特异性时,类型概念的设定会相当有效果。
村上正二把北亚的游牧社会二分为「古代的游牧社会」和「中世的游牧社会」,以此来讨论游牧社会历史变迁的进程。他分析说,古代游牧社会因为保持氏族共同体的旧貌,因此相当脆弱;但中世游牧社会将氏族加以解体重编,因此相当坚固。他又举出,蒙古游牧社在进入明清时代后迈入安定期、甚至是衰颓期,以致「对中国社会不再构成威胁」这一特征,并强调清代蒙古史研究的重要性。按照他的理论,游牧国家和中国王朝对立时会形成威胁,但被中国纳入内部时,就会产生涵化作用。
在这之后,清代的蒙古史研究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在此就略而不提,但对征服王朝论的关心,则是历久不衰。一九七三年,吉田顺一针对作为战后日本北亚史学界主要研究课题的征服王朝与北亚历史发展,作了如下段的总结。
吉田顺一认为,村上正二等日本历史研究者「看见了魏复古理论中完全不曾注意到的倾向,也就是把征服王朝纳入北亚史的发展过程中加以掌握,并将之理解成此等发展的某种归结」。他更进一步说,无庸置疑地,日本的研究者让吸收人类学者涵化论与同化论、并加以适用的魏复古理论妥当性得以深化。魏复古关注在异民族掌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变貌,却没有想到征服王朝的出现是北亚游牧社会发展的结果;但日本研究者却能够将征服王朝的出现,定位在北亚史的发展进程之中。
吉田顺一力陈,目前对于最终发展成征服王朝的游牧社会内部构造仍未解明,有必要进行更深一层的研究。因此,他一边统合战前日本人对游牧社会的相关调查,一边积极对游牧社会的实际状况展开研究。
话说回来,对于和满洲人携手建立清朝的蒙古,近年的历史研究者又是怎么看待的呢?这个问题往往和清朝时代的蒙古史究竟该视为「蒙古史」、还是该定位为「身为中国历代王朝史一环的清朝史当中的一部分」,有着密切的关联。
杉山正明在《大蒙古的世界》(一九九二)这本着作中,针对清朝与蒙古的关系作了以下的分析。
清朝的皇帝同时具有「中华帝王」和「蒙古大汗」两重面貌。满洲皇帝从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那里,接受了自大元王朝兀鲁思以来的「传国玉玺」,象征同时具备蒙古大汗的地位。清朝从建国起,直到末年的太平天国之乱、捻乱、鸦片战争等,一直仰赖蒙古军的战力。从这个事实来看,清朝的历史直到最后,都有着蒙古的身影。
杉山正明之后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一九九七)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二○○五)中,力陈应当从超越中国史、与世界史连动的立场和视角出发,对北亚游牧民的历史重新思考。另一方面,近年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征服王朝」的概念应该更往西扩大。换言之,就是从欧亚史整体规模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整个北亚、中亚的历史。
另一方面,片冈一忠针对清朝对新疆的统治方法进行检讨,得到这样的结论:身为征服王朝的清朝,在面临到俄罗斯与英国等西欧列强切断其与周边各藩部的关联时,意识到唯有采取将之纳入汉族(中国内地)怀抱,以寻求藩部与内地一体化,才能避免失去藩部。 若是依循这种思考方式,则清朝末期各藩部的历史,随着外部势力、特别是西欧列强的涉足,整体而言愈来愈有被纳入中国史一部分的倾向。当然,随着清朝瓦解而独立的蒙古高原一部分,则有着完全相反的发展。
内在的历史认知
游牧民族的历史究竟是北亚史发展的结果,还是应该从它与中国史的连动去加以理解?上面介绍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诸多论述。然而,这些概念都不是游牧民族自己所提出,换言之,是从外部展开的观点。既然如此,那身为当事者之一的蒙古人,对这个问题又有着怎样的认知呢?
蒙古自古以来就有口语传述历史、书写历史的传统。在此根深蒂固的传统之下,蒙古人自十三世纪起便留下许多文献资料。在众多编年史——比方《蒙古秘史》中,多半是口述纪载,全面强调王权天授的传统宇宙观。到了十六世纪以后,开始出现将成吉思汗家族的神圣起源与印度、西藏王室结合的著作;这种宁可向印度与西藏寻求神圣起源,却不向中国传统找寻的现象,相当值得注目。
这些历史著作与受到易姓革命思想影响的中国王权观,有着显著差异。比方说,在一六六二年成书、写到蒙古受清朝统治为止的史书《蒙古源流》,甚至不把蒙古放在中国历代王朝的位置当中;而像《蒙古源流》结合北亚萨满教固有的王权天授思想和藏传佛教,这种认知,在十六世纪以降的蒙古编年史可是蔚为主流。
在蒙古,有将历史上的大小事用口语传述下来的传统。这种「口语传述」,不是针对个别历史事件进行传述,而是一种明示其因果关系、由动态社会变化所构成的认知。自十三世纪蒙古拥有文字之后,「口传」的行为,遂转变成编年史诞生的原动力。换言之,这些编年史理所当然带有相当大的「口传」特征。我想将这种「传述历史的行为」,定义为对历史的内在认知。为了一窥这种历史认知的方式,我们必须针对「历史的口述方式」以及编年史的记述两方面,同时进行检讨。
中国史化的蒙古「地方史」
蒙古史究竟该视为中国历代王朝史的一部分,还是北亚自己的历史?姑且不提这个论争,如我前文所言,蒙古人自己写的编年史,经常是从独立于中国史之外的观点来叙述。现在,蒙古族的一部分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形成一个自治区以及众多的自治州、自治县。在中国,由政府主导新写成的「蒙古史」类型作品,和前述编年史的史观有着很大的差异——简单说,有尽可能把蒙古史当成「中国史的一部分」来书写的强烈倾向。从这种新撰写的变质「蒙古史」中,产生出一套对中国历史的认知,以及对蒙古历史的不同看法。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被定位为展现王朝正统性的产物;每当政权交替,新王朝必定会把修史作业当成重要任务。他们会将灭亡的前王朝数据,按照对新王朝有利的方式加以编纂,从而为王朝正统该如何树立提出证明。修史作业往往会全面性地宣扬自己比历代王朝、特别是前王朝或前政权更为优秀之处;在现代中国,它所强调的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他们把着力点放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上,当然也会反映出当时的执政者,为了巩固自己权力基础而推出的种种政策。这阵子大肆哄传的「对日史观」,说穿了也不过是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正统性,所推出的论调罢了。
即使在现代中国,把修史视为重要任务的理念也没有任何变化。从通史与地方史(志)的编纂,可以确认以下说法。
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通史简编》于一九四九年出版。之后,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国史稿》,在郭沫若的主导下,持续进行撰写与出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不只是前王朝的历史,将历代王朝交替的潮流加以体系化的通史编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远比撰写单一王朝的历史更加重要。除了国家层级的《中国通史》以外,在各少数民族方面,也有很多以「某族通史」形式写成的作品。本章就要来探讨《蒙古族通史》这部史书。
还有另一种史书,是所谓的地方史(志)。地方史(志)的传统相当古老,然而其编纂主旨并不因此与通史大相径庭。关于某地的方志情报,当然比通史更加详尽,也有很多对通史加以补足的内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方志自然也不例外,以下我们会列举出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的史书。
有趣的是,修史作业仰赖的,正是司马迁《史记》以来的「纪传体」体制。这种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构成的史书结构,在现代的通史、地方史(志)的编纂中仍然维持不变。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超过数千种的通史与地方史(志)的编纂方针、内容架构,其实都免不了大同小异。
用什么语言来书写历史?
现代中国修史作业的过程中,语言的使用值得关注。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要撰写某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时,如何使用汉语以外的语言书写,其方法就相当值得质疑。就历史上而言,那些被定位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民族,他们的记录和汉文数据有着根本上的差异。相对于汉文数据中众多有意歪曲、偏向对中华有利的记述,以少数民族语言书写的文献,根本就是另一片天地。因此,当编纂通史、地方史(志)要活用少数民族文献的时候,如何取舍选择,就相当值得玩味。
我们就以蒙古族为例来看。现行的《蒙古族通史》是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主导下,以汉语为主写成,于一九九一年出版。之后在一九九五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这部通史的蒙古语版本,执笔者包含了汉人与蒙古人的史家。
地方史(志)的编纂也是如此,至少我可以在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确认到这点。从一九八○年代初期到一九九○年代中期,地方史(志)的编纂被当成国家计划,在这两个自治区加以推进。当时编纂的状况是,在汉人编纂者底下,配属大量的译者进行作业。这些译者负责将庞大的少数民族语言数据翻译成汉语,而汉族的执笔者主张,翻译出来的资料只能拣选合乎国家编纂方针的内容来使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出版的地方史(志)、地名图志等,几乎都是用汉语写成。当地领导人主张,因为各民族对地名的由来与解释,以及历史事件的见解无法统一,所以将之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的工作必须推迟;然而,原因并不止于此。
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间,维吾尔人吐尔贡.阿勒玛斯撰写了《维吾尔人》、《维吾尔古代文学》、《匈奴简史》等三本着作;在书中,他主张维吾尔人是匈奴的子孙、长城以北不是汉人的领土。他的著作因为不合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以及社会主义史观、涉嫌分裂祖国、宣扬泛突厥主义而遭到批判,并被列入禁书。因为遭到查禁,所以我到现在也还没能拜读这三本着作。
用汉语书写的通史、地方史(志)的出版,必须接受党、政、军各相关机构的评判与审查,在政策上被判定为合格时,才能够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然而,就算还原成少数民族语言,这些史书也没有引用文件资料的背景说明,因此不能充分复原资料。不只如此,当这些内容不被少数民族认同的时候,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的工作就会停滞不前。在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史(志)很少被翻译成蒙古语、维吾尔语或哈萨克斯坦语,就是这种政治背景所导致。
口传历史的重要性
由国家主导的「某族通史」与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史,都是为了中国这个国家而服务。相对于此,由少数民族自己撰写、或是口语传述的历史,则未必会意识到中国的国家正统性。
在我迄今为止的调查中,除了关注少数民族如何透过口语,传述自己视作「历史」的过去大小事外,也十分留意编年史的书写方式。这些调查既然是以现今的少数民族为对象,那么对少数民族历史认知的观察,自然也是一种现在进行式。严格来说,这种认知既是以过去的「事实」为对象,那么现在的人们,理应不可能完全亲炙过这些「事实」;然而,因为历史与社会有其延续性,所以该社会现今的成员仍会把自己放在当事者的位置上。因此,我也把现在的蒙古人视为当事者,打算用侧写十九世纪末蒙古史的方式,来呈现出蒙古人对历史的认知。
关于十九世纪初期到二十世纪五○年代的蒙古历史演变,不只留有为数众多的资料,在史学的先行研究上,也累积了相当丰厚的资产。我所用的方法,并不是对过去的事实进行「科学、客观」的复原,而是关心蒙古人如何「传述过去」。换言之,我留意的是蒙古人对过去大小事所进行的设定、以及传述的方式。
既然如此,那留意历史或是过去大小事的口语传述方式,其意义又何在呢?
历史学家成田龙一在最近的作品《「历史」是如何被传述的?》当中,提出了以下的论点:历史是创造出民族国家、并支撑起其架构的重要装置。战后的日本历史学——比方说教育第一线使用的历史教科书,把事件的复原当成是历史的本质;之后则有一部分的研究者认为,事件会随着不同的解释而产生出不同的样貌,因此,「历史」说到底不过就是各自不同的「解释」罢了。
我自己的看法是,倘若单单只是对事件进行复原,绝对无法贴近当时人们的实际心理状态。尽管如此,「历史只是解释」这种议论,也有让人无法苟同之处。因此,我想做的是,重新回到原点,关注当事者如何选择、设定、并且更进一步传述过去的大小事件。简单说,就是在传述所呈现出来的样貌中,设法贴近当事人的心灵与生活状态。
虽然我说要关注「十九世纪的蒙古」,但要以全蒙古为对象,还是相当困难。因此,我主要聚焦在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地区及其周边。在鄂尔多斯地区所发生的事件,绝非像中国主张的那样,是单单放在「地方史」层级便可解决的问题。它们不只是清王朝史具体的一部分,更进一步和亚洲整体的国际情势彼此连动。本章就要举出其中典型的事例之一——将多民族、多宗教卷入其中的「回乱」。
(本文摘录自《蒙古与伊斯兰中国:一段贴近民族心灵的旅程》,八旗文化出版。书味转载稿件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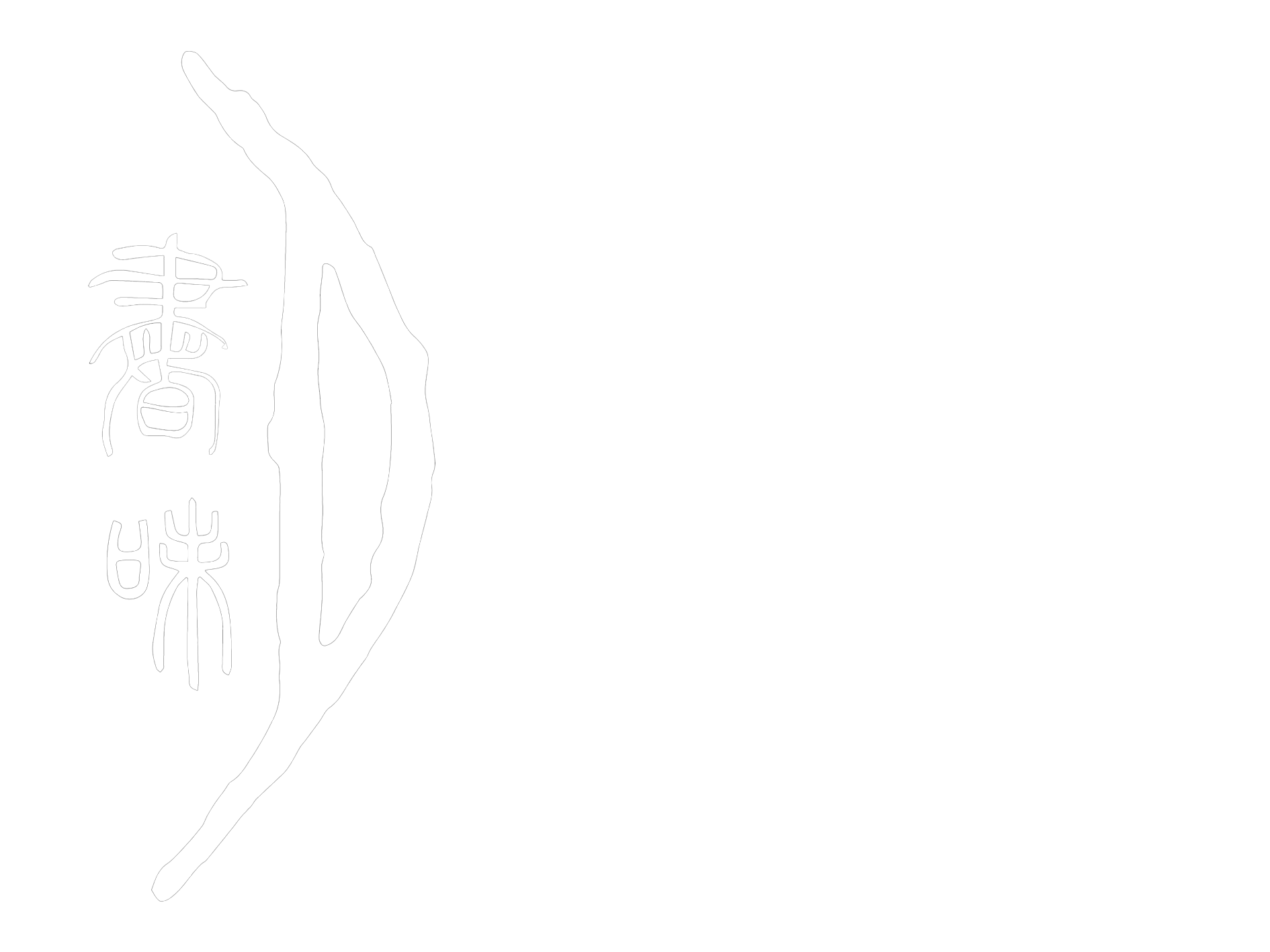
南归
2024-08-17 00:33视角独特,能帮助我们更全面的看待该历史事件。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