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便是一般与事实相符的刻板印象,真实的阿拉伯世界就是比这些刻板印象更极致、更疯狂。比如,沙乌地阿拉伯盛产石油,油比水便宜。便宜到什么程度呢?政大阿语系教授郑慧慈说,「路边加油站的油漏了,也没人处理。」反倒是浇花水浇太多,水流到地面上,会有警察上门关切。
水资源如此珍贵,但沙乌地阿拉伯的水费因政府支助所以仍属低价。这个石油富国的淡水全靠海水淡化而来,成本极高,沙乌地阿拉伯却曾一度是全世界小麦产量第二高的地区,农作灌溉用水全是昂贵的淡化海水,富国的霸气展露无遗。
郑慧慈在80年代曾留学阿拉伯世界,是第一位在沙乌地阿拉伯拿到博士学位的台湾女性。在异国念书期间,她也见识到阿拉伯世界富有的景况,她在新书《阿拉伯奇想千年》谈到去同学家作客,入口玄关像饭店大厅,富丽堂皇,室内的装潢、摆饰,眼见凡是黄色的都是黄金,白色的是银,至于透明的,千万别以为是玻璃,是水晶。
来自80年代封闭岛国的弱女子,对于宛若天方夜坛里奢华皇宫的场景,一方面感到赞叹,一方面:「觉得好自卑喔。」同学会因为贫富阶级而歧视妳吗? 「绝对不会,阿拉伯人很慷慨,尤其对朋友,几乎是热情到把你当家人。」郑慧慈初到异地,因为适应问题曾经连哭了一个月,哭到后来,同学们只要见她脸色稍微不对,便上前关心:「怎么了?有什么心事要说啊。」问到她都不好意思心情不好。
阿拉伯人对「家」的界限非常严格,不轻易在家招待朋友,郑慧慈却跟阿拉伯人特别投缘,多次到朋友家作客,甚至学校老师还开放家里书房让她读书。阿拉伯人也爱面子,作东时会把家中最好的一切全端出来,某次在游牧民族贝都因人家作客,全羊大餐被端了上来,吃一半,郑慧慈好奇摸了摸羊头。主人立刻站起来,准备到帐棚后方再宰一头羊。
原来,在贝都因人家,客人若碰了羊头,意思是还没吃饱,需要其他食物。任凭郑慧慈如何向主人解释自己是无意碰到羊头,主人仍坚持杀羊。
异国的趣事怎么也说不完,趣闻背后常有其社会脉络和历史背景,《阿拉伯奇想千年》不只是旅人的异国猎奇,更提供一个深刻理解他人的窗口。我们对阿拉伯世界女性的刻板印象是:黑袍、蒙面纱。郑慧慈说,「事实上,约旦很西化,女性穿着跟西方无异,只有在沙乌地阿拉伯女人才会做这种打扮,这和他们的宗教派别有关。」
好莱坞电影里,中东女子穿着露肚皮的舞衣风情万种跳舞则是,假的! 「传统的阿拉伯女子不可能有这种打扮,肚皮舞是传统阿拉伯舞蹈,但跳的时候还是穿黑袍,顶多腰间系上一条丝巾。」原来,露肚皮的异国舞娘是好莱坞娱乐化的想像。
而黑袍下的阿拉伯女人,是什么模样呢?郑慧慈形容,当时学校教室入口处有一个换衣间,供女学生把「阿巴雅」(abaya,黑袍)脱下,而褪下黑袍的阿拉伯女人打扮入时,身上穿戴名贵首饰。全身包紧紧,阿拉伯的年轻男女们要如何追求异性,难道他们全不在乎外表?
她提了一个阿拉伯女同学的例子,「我同学的老公会和她结婚,只是因为有天看到司机来接她下课,她拉车门上车的动作非常优雅,于是爱上这个女孩,找人提亲。」人是视觉动物,眼睛业障重,也许正因为什么都看见了,所以也什么都没看见,反倒是什么都没有,却什么都看见了。

沙乌地阿拉伯女性在公开场所必须穿着黑袍,黑袍下是美丽的衣着和首饰(图/ Tribes of the World @flickr)
热爱阿拉伯文学的她,在书中还引了一段阿拉伯古情诗:「我对她的爱,犹如你无法喝水时之爱水。」如此直白的情诗也太不浪漫了吧? 「这是阿拉伯文学的风格,很直接。」而男女交往则又是另一回事,郑慧慈说,阿拉伯男人追求女子会抄古诗来表达爱意,遇到心仪的女子,连讲话都变得文诌诌。
谈到阿拉伯的女性地位,同时间书市上另一本《蒙面女人,漂亮男人》是一名台湾年轻女子在阿拉伯世界的生活纪录,里面提及许多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好比丈夫死了,妻子生病不能出国就医,后来活活病死,不能出国竟是因为没有丈夫的签名担保,还有近年媒体不断出现的「荣誉谋杀」(又称羞耻罪):家中兄长杀害他们认为有辱家风的女性家人。这些谋杀案最后都被轻判。
郑慧慈用西化过程中、传统宗教力量的反扑来理解这件事,「羞耻罪是『落部法』,并不是『宗教法』,这种行为是误解了《古兰经》。」从20世纪土耳其凯末尔将军的「西化」、90年代美国介入波湾战争、甚至到近年的茉莉花革命,伊斯兰世界的传统宗教价值都不断被挑战,「在整个西化过程里,传统被挑战,然后传统力量反扑,主张要打造一个纯净的伊斯兰价值世界,所以会看到这几年突然羞耻罪案件变多了,这在以前并不多见。又好比现在的伊斯兰国(IS),很多阿拉伯人虽然不赞成这种组织,但同时又认为它有存在的必要(指维护传统价值)那种矛盾心情。」
在阿拉伯世界生活这么久,郑慧慈似乎也看出其中各种矛盾情结,「阿拉伯人慷慨好客,但另一面就是铺张浪费,请客时的菜常常只吃几口就倒掉了。」女性看似地位低落,但也不如外界想像的骇人,「羞耻罪是少数个案,大部分阿拉伯人还是很尊重女性,像是聊天时,男人不会跟朋友的妻子有眼神交会。我去朋友家作客,连朋友的父亲都会回避。」宗教规范阿拉伯人,使他们展现热情善良的一面,但宗教同时也是阿拉伯极端宗教主义者的驱动力。
已经回台任教超过20年了,郑慧慈还是难忘阿拉伯,每隔一阵子就要吃阿拉伯菜以解「乡愁」。尽管深爱阿拉伯文化,她对于严格的斋戒月(有些教派连吞口水都有严明要求)、路上的宗教警察(她曾露出小腿被警察要胁逮捕)都有不快的回忆,但这些仍不减他对阿拉伯的热爱。
毕竟,太过于了解一个地方是无法纯粹的爱上它,而世间大部分的爱也大抵如此,因为太清楚里头各种无解的矛盾、疙疙瘩瘩,最后这些爱都带着微微的刺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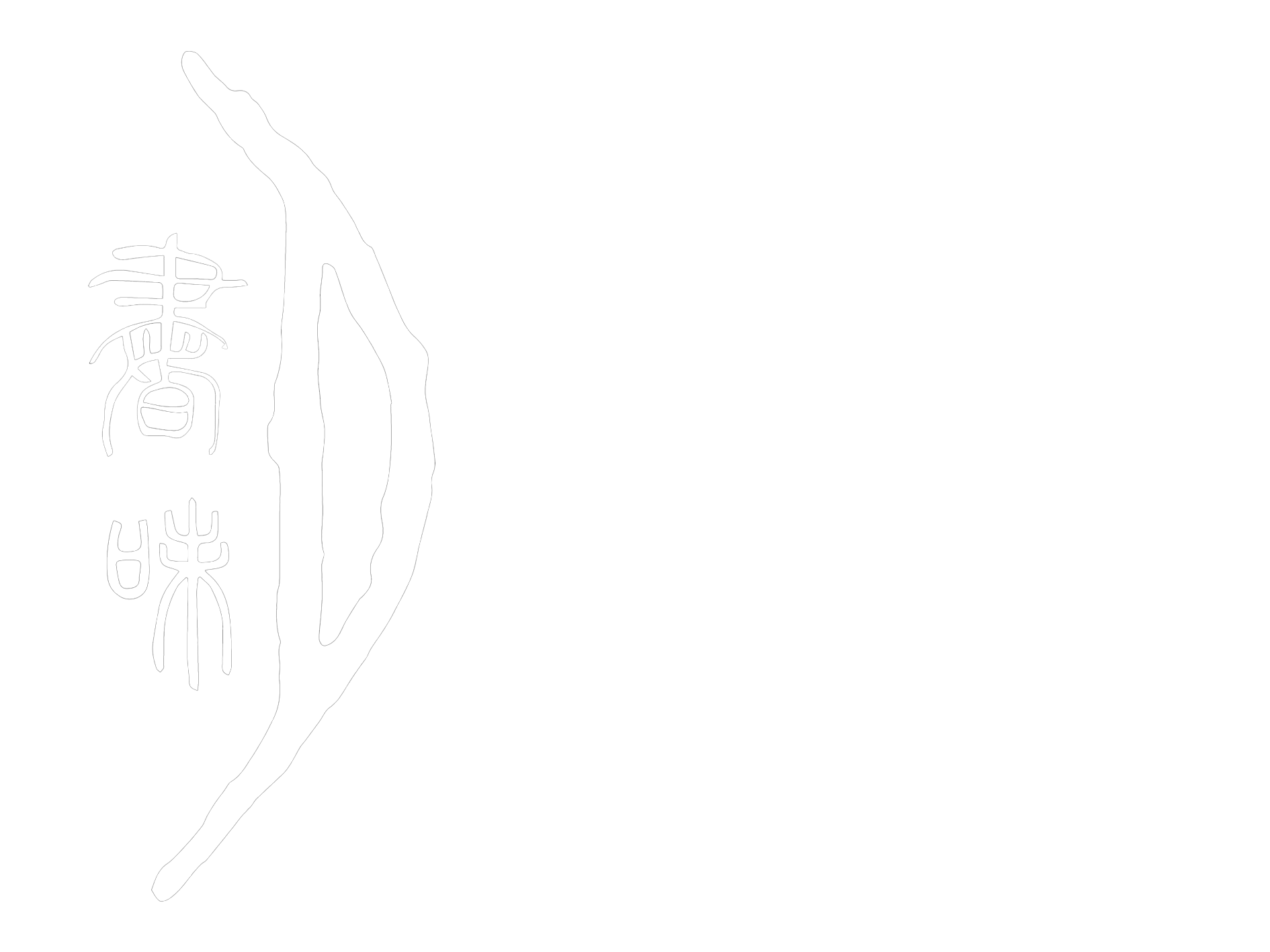
暂无评论
来做第一个评论的人吧!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