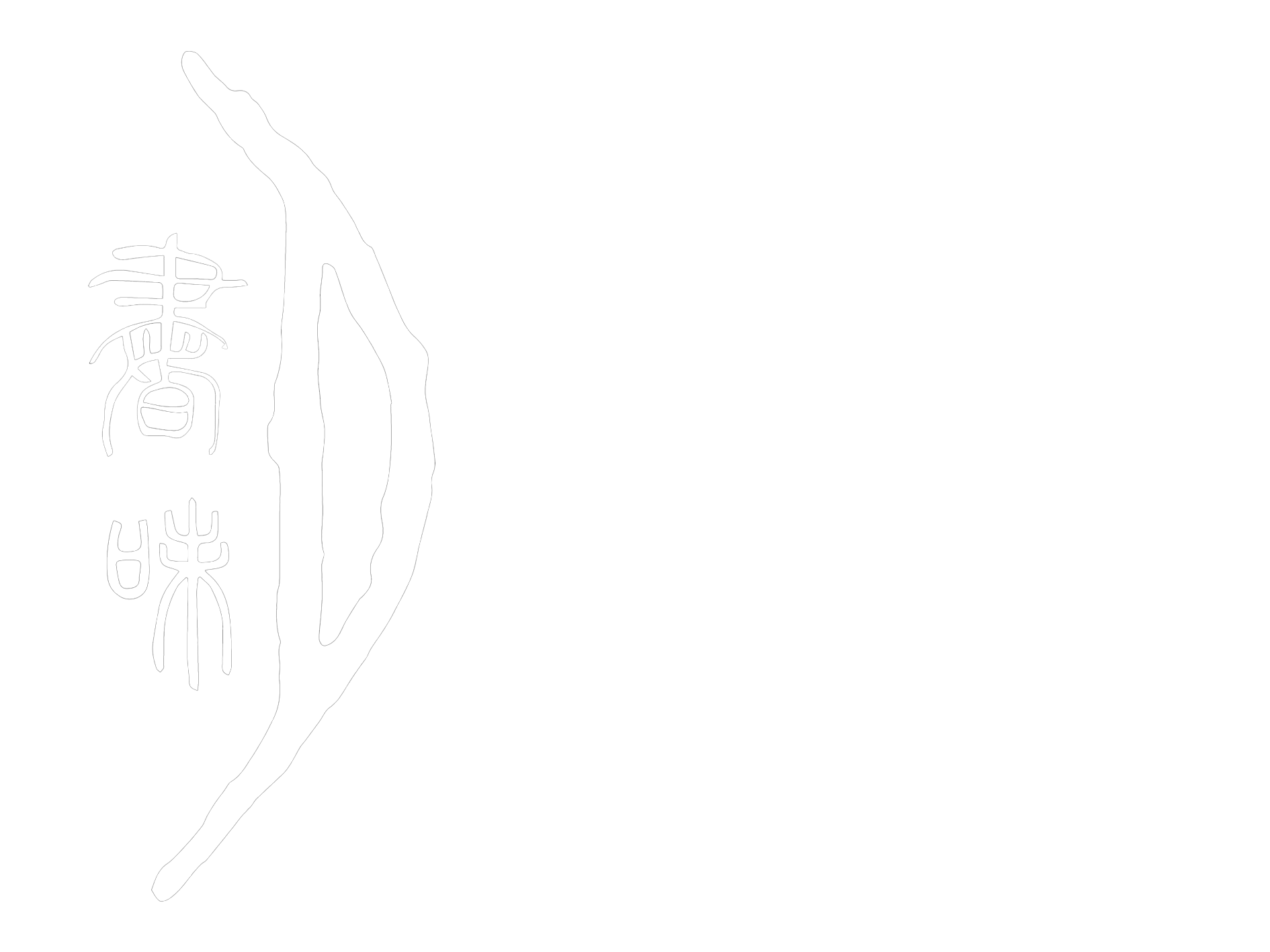一生都在等待——搜寻一排排无人认领的尸体
赛拉•俾路支是俾路支省数千名寻求答案的女性之一,她们声称这些男性被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强迫失踪 赛拉•俾路支 (Saira Baloch) 15 岁时第一次踏进太平间。昏暗的房间里,她只听到抽泣声、低声的祈祷声和脚步声。她看到的第一具尸体是一名男子,似乎遭受了酷刑。他的眼睛不见了,牙齿被拔掉了,胸口有烧伤的痕迹。 “我无法看其他尸体。我走了出去,”她回忆道。但她松了一口气。这不是她的兄弟——一位警察,自2018年在巴基斯坦最动荡的地区之一俾路支省的一次反恐行动中被捕以来,已失踪近一年。停尸房里,其他人继续拼命搜寻,扫描着一排排无人认领的尸体。赛拉很快又开始这般残酷的日常,一遍遍地走访停尸房。它们都一样:日光灯闪烁,空气中弥漫着腐烂和消毒剂的恶臭。每次去,她都希望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七年过去了,她仍然没有找到。 活动人士称,过去二十年里,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失踪了数千名俾路支族人,据称他们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拘留,或在打击数十年来的分离主义叛乱的行动中被绑架、折磨和杀害。 巴基斯坦政府否认了这些指控,坚称许多失踪人员已加入分裂组织或逃离该国。 有些人多年后归来,身心俱疲,但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一些人被发现埋葬在俾路支省各地的无名坟墓中,尸体严重毁损,无法辨认身份。 还有一些跨世代的女性,她们的生活都在等待中。 他们参加抗议活动,无论老少,脸上都写满悲伤,手里举着逝去亲人的褪色照片。BBC记者在他们家中采访时,他们用缺口的杯子给我们端来红茶——苏莱曼尼茶,语气中充满了悲伤。他们中的许多人坚称,他们的父亲、兄弟和儿子是无辜的,只是因为公开反对国家政策而成为攻击目标,或被当作一种集体惩罚。 赛拉说,每次敲门声都给她带来希望 Saira 就是其中之一。 她说,在向警方和政界人士询问她弟弟的下落后,她开始参加抗议活动。2018年8月,穆罕默德•阿西夫•俾路支(Muhammad Asif Baloch)与其他10人在阿富汗边境城市努什基(Nushki)被捕。第二天,他的家人在电视上看到他时才得知此事,当时他看起来惊恐万分,衣冠不整。 当局称,这些人是“逃往阿富汗的恐怖分子”。穆罕默德的家人称,当时他正与朋友们野餐。赛拉说穆罕默德是她“最好的朋友”,风趣幽默,总是开朗乐观——“我妈妈担心她会忘记他的笑容。”失踪那天,赛拉在学校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她兴奋地告诉了哥哥——她“最大的支持者”。穆罕默德曾鼓励她去省会奎达上大学。 “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第一次去奎达是为了抗议要求释放他,”赛拉说。与她兄弟一起被拘留的三名男子于 2021 年获释,但他们没有谈论发生的事情。穆罕默德再也没有回家。 通往荒地的孤独之路 进入巴基斯坦西南部的俾路支省,感觉就像踏入了另一个世界。它幅员辽阔,覆盖了巴基斯坦国土面积的44%,是巴基斯坦最大的省份,土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煤炭、铜和黄金。它沿着阿拉伯海延伸,隔海与迪拜等地相望,迪拜从沙漠中拔地而起,如今已成为一座座金碧辉煌、摩天大厦林立的城市。 但俾路支省依然停滞不前。出于安全原因,许多地方的出入受到限制,外国记者经常被拒绝进入。四处旅行也很困难。道路漫长而荒凉,穿过荒山和沙漠。随着道路越走越远,基础设施也越来越薄弱,道路被少数车辆留下的泥土路所取代。电力供应不稳定,水资源更是匮乏。学校和医院状况堪忧。在市场上,男人们坐在泥店外,等待着难得一见的顾客。在巴基斯坦其他地方,这些男孩或许梦想着一份事业,而如今,他们却只谈论着逃离:逃往卡拉奇,逃往海湾地区,逃往任何能让他们摆脱这种缓慢窒息的地方。 1948 年,在英属印度分治后的动乱中,俾路支省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尽管一些有影响力的部落领袖反对,他们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些抵抗力量逐渐演变成武装力量,多年来,人们指责巴基斯坦掠夺了这片资源丰富的地区,却没有对其发展进行投资,这进一步加剧了抵抗力量的动乱。被巴基斯坦等国家列为恐怖组织的俾路支解放军(BLA)等武装组织加大了袭击力度,针对安全部队的爆炸、暗杀和伏击事件更加频繁。 本月初,俾路支解放军在博兰山口劫持了一列火车,劫持了数百名乘客。他们要求俾路支省释放失踪人员,以换取人质。此次围攻持续了30多个小时。据当局称,33名俾路支省解放军武装分子、21名平民人质和4名军事人员被击毙。但相互矛盾的数据表明,许多乘客仍然下落不明。 人们普遍认为,该省的失踪事件是伊斯兰堡镇压叛乱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了压制异议、削弱民族主义情绪和对俾路支省独立的支持。许多失踪人员疑似为俾路支民族主义团体的成员或同情者,这些团体要求更多自治或独立。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已知政治立场的普通民众。 失踪人员: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在这种情况下失踪 俾路支省首席部长萨法拉兹•布格蒂 (Sarfaraz Bugti) 向 BBC 表示,强迫失踪是一个问题,但他否认大规模发生强迫失踪的说法,称其为“系统性宣传”。“俾路支省的每个孩子都听到过‘失踪人口,失踪人口’的声音。但是谁来决定是谁失踪了呢?“自我失踪也是存在的。我该如何证明一个人是被情报机构、警察、FC,还是其他人,或者我,或者你,带走的?” 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中将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正在系统地解决失踪人员问题”。他重复了政府经常分享的官方统计数据——自 2011 年以来,俾路支省报告的 2,900 多起强迫失踪案件中,80%已得到解决。活动人士给出的数字更高——约为 7,000——但没有单一可靠的数据来源,也无法验证双方的说法。 “沉默不是一种选择” 像 Jannat Bibi 这样的妇女拒绝接受官方的数字。她继续寻找儿子纳扎尔•穆罕默德 (Nazar Muhammad),她声称儿子于 2012 年在一家酒店吃早餐时被带走。“我到处找他,甚至去了伊斯兰堡,”她说,“结果却遭到殴打和拒绝。”这位 70 岁的老人住在奎达郊区的一间小泥屋里,距离一座为失踪者修建的象征性墓地不远。詹娜特经营着一家小店,卖饼干和牛奶盒。她经常付不起公交车费去参加要求提供失踪人员信息的抗议活动。但她会尽可能地借钱,这样才能坚持下去。“沉默不是一种选择,”她说。Jannat Bibi 表示,她试图寻找儿子,但无果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包括那些与我们交谈过的家人——在 2006 年后失踪。同年,俾路支省一位重要领导人纳瓦布•阿克巴尔•布格蒂 (Nawab Akbar Bugti) 在一次军事行动中丧生,导致反政府抗议活动和武装叛乱活动增加。政府采取严厉措施予以应对——强迫失踪事件增加,街头发现的尸体数量也增加。2014 年,在奎达以南 275 公里(170 英里)处,赛拉居住的胡兹达尔市附近的一个小镇图塔克发现了失踪人员的集体坟墓。尸体惨不忍睹,难以辨认。图塔克的惨状震惊了整个国家,但俾路支省的民众对这种恐怖并不陌生。 马赫朗•俾路支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民族主义领袖,他为俾路支人的权利而奋斗,但于 2009 年初失踪。阿卜杜勒•加法尔•兰戈夫曾在巴基斯坦政府工作,但为了倡导俾路支省的更安全而辞职。三年后,马赫朗接到一个电话,说他的尸体在该省南部的拉斯贝拉区被发现。“父亲的遗体运到时,他还穿着同样的衣服,只是现在破烂不堪。他遭受过严重的折磨,”她说。五年来,她一直梦见父亲临终前的那些日子。她去墓前拜谒父亲,“是为了让自己相信他已经不在人世,没有遭受任何折磨。” 她拥抱着他的坟墓,“希望能感受到他,但却没有”。被捕时,马赫朗经常给他写信——“很多信,我还会画贺卡,在开斋节那天寄给他”。但他把贺卡退回来,说牢房里放不下这么“漂亮”的贺卡。他想让她把贺卡留在家里。“我仍然怀念他的拥抱,”她说。 马赫兰说,父亲去世后,她的家庭世界就“崩溃了”。据家人称,2017 年,她的兄弟被安全部队抓获,并被拘留了近三个月。“太可怕了。我让我妈妈相信,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事不会发生在我弟弟身上。但最终还是发生了,”马赫朗说。“我不敢看手机,因为里面可能是我弟弟尸体在某个地方被发现的消息。”她说,她和母亲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力量:“我们那间小屋是我们最安全的地方,有时我们会坐在那里哭上几个小时。但在外面,我们是两个坚强的女人,不会被压垮。”正是那时,马赫朗决定与强迫失踪和法外处决抗争。如今,这位32岁的年轻人不顾死亡威胁、法律诉讼和旅行禁令,领导着这场抗议运动。“我们想要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受迫害地生活的权利。我们想要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权利。我们希望这种恐惧和暴力的统治结束。”Mahrang 在她父亲的坟前 马赫朗警告说,强迫失踪只会激起更多的反抗,而不是压制它。“他们以为抛尸就能结束这一切。但谁能忘记以这种方式失去亲人的痛苦呢?没有人能承受这种痛苦。”她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确保没有母亲不得不把孩子送回家里,让他们担惊受怕。“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抗议营里长大。这要求过分吗?”马赫兰在接受 BBC 采访几周后于周六早上被捕。 此前,奎达市内埋葬了13具无人认领的尸体,疑似失踪人员,她当时正在领导一场抗议活动。当局声称,这些尸体是博兰山口火车劫持事件中被击毙的武装分子,但这一说法无法得到独立核实。此前,马赫朗曾表示:“我随时都可能被捕。但我并不害怕。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就在她为自己想要的未来而奋斗时,新一代人已经走上街头。10 岁的马苏玛紧紧抓住书包,穿梭在抗议人群中,她的眼睛扫视着每一张脸,寻找一张像她父亲的脸。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男人,以为他是我父亲。我跑向他,然后才意识到他是别人,”她说。“每个人的父亲下班后都会回家。但我从来没有找到过我的父亲。”据称,安全部队在奎达的一次深夜突袭中带走了马苏玛的父亲,当时她只有三个月大。有人告诉她母亲,他会在几个小时后回来,但他始终没有回来。如今,马苏玛参加抗议活动的时间比在课堂上的时间还多。她父亲的照片一直陪伴着她,安全地放在她的书包里。每次上课前,她都会拿出来看一看。“我总是想知道父亲今天是否会回家。” 她站在抗议营地外面,和其他人一起高呼口号,她瘦小的身影消失在悲痛的家庭人群中。抗议活动结束后,她盘腿坐在一个安静角落的薄垫子上。口号声和车流的喧嚣渐渐远去,她拿出叠好的信——那些她写好却永远寄不出去的信。她抚平褶皱时手指颤抖,然后用笨拙、不确定的声音开始阅读。“亲爱的巴巴•詹,你什么时候回来?每当我吃饭喝水的时候,我都会想你。巴巴,你在哪里?我太想你了。我孤身一人。没有你,我睡不着。我只想见到你,看看你的脸。”